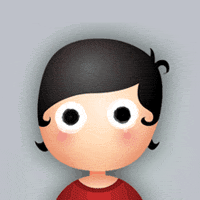唐仪天∣沙尘暴
唐仪天
甘肃省作协会员 民勤县文联副主席 民勤县作协副主席。
民勤县苏武乡五坝村农民,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人民文学》《飞天》《朔方》《北方作家》《西凉文学》《郑州晚报》《北海日报》等多家报刊发表散文多篇。作品入选甘肃文化出版社《行走大地》。入选《飞天》60年典藏,入选《西凉文学》50期刊庆典藏。2011年与文友合作出版散文集《镌刻在绿洲的记忆》。
2013年出版《唐仪天散文》。荣获第五届黄河文学奖散文二等奖;《飞天》新兴花卉杯散文三等奖,连续两年荣获武威市散文创作一等奖。获民勤绿洲文艺奖。
■ 听雨楼
沙尘暴
我无法逃避沙尘暴地追袭,就像记忆无法逃脱我的追溯。在一次次呼啸而来的沙尘暴里我惊怵、恐慌,但我又不得不抖落烟尘,仓促急迫地收拾残局,抚慰那些在沙尘暴中顽强存活下来的庄稼。我是农民,我没有理由在一场大风走过村庄之后,舍弃土地,背离庄稼甩手而去。
在这个村庄里,我经历了无数次不期而至的沙尘暴,沙尘暴一而再再而三地侵夺过我的庄稼,糟践我的村庄,但我无法把这些情况一一记录在案。那些风却在它们遁迹消弥之后,反复地掠过我记忆的天空。面对苍茫宇宙,面对严酷的大自然,人是弱小的,既使人们操老子骂祖宗也是干淡,再日能的人也无法薅住沙尘暴的尾巴,过一把武松打虎的瘾。沙尘暴照样扬威耀武,照样气吞山河如虎。
记忆中最早一场风,是在我六、七岁那年掠过村庄的,那风俨若行走的波涛,排山的巨浪,自西天汹涌而止,低矮破旧的村庄,在大风出现之后变得更加灰暗残败。一霎间风像一口巨大的黑锅罩住了村庄,村庄顿时进入沉沉的黑夜。风嚣张地打着口哨,把苫在屋檐上的柳条摞子摔下来,把垛在院外的草垛撕下来,草棵子们长了脚一样没命地飞奔在大道上,如溃逃,如赴会。
那个夜晚,我爬在被窝里惊恐地聆听着风的吼叫,煤油灯染黄了我家里黑暗的小屋,空气中弥满了细细的灰尘。我听见我家屋顶有一种腾腾欲飞的声势,屋子更是抖动不安。一种来自地层深处的声音牵痛了父母的神经,那是树木根须断裂时的疼痛,沉闷、干脆,似乎还有些不情愿。
第二天清晨,风还在嘶鸣,但明显地减弱了力量,风刮乏了。刮乏了的风,像跑得太快的人,收不住势,不得不顺着劲跑下去。我家院墙外的两棵一抱子粗的沙枣树,斜斜地横在了地上,沟沿上的树也残遭了风的打击,有的断了头,有的被连根拨起、掀翻。村子灰楚楚地坐在大地上,宛如大病未愈的患者,粗粗地喘着气……
这样的风在民勤绿洲上司空见惯,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们最初领略这样的大风时,还没有给它一个科学专业的称谓,许多年来人们是根据风的颜色为它命名为“黄风”、“黑风”,或者以风力的大小称为“大风”或者“老风”。而“浮尘”、“沙尘暴”、“特强沙尘暴”是近年来科学专业的术语。但是,多么雅致或者恐怖的称谓,都无法消去我们长久以来对沙尘暴的愤怒,这样的风一旦走过村庄,我们的农业将无法幸免地遭遇程度不同的损害,同时也会给我们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谁也无法拒绝它的造访。
我的记忆里之所以抹不去那场沙尘暴的侵袭,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超乎常人的记忆或者智慧,那场风毫不留情地把院外的两颗沙枣树掀翻,确实有些欺人太甚,无疑给我们捉襟见肘的日子雪上加了霜。在那些生活极度困难的时代,两棵沙枣每年都以丰厚的产量回报我们的期待。羊奶头大的沙枣香甜可口,富含淀粉,我们常常吃得头顶冒汗。那场沙尘暴怀着深深的仇恨感,怀着丑恶的嫉妒心,趁夜搡倒了我们心中的圣树,然后仓皇逃窜。我已说不清那场沙尘暴对农田造成了怎样的影响,那是大人们的事。而陆陆续续的大风几乎弥盖了我记忆的晴空,它们大都发起于每年的冬春季节,带着鬼哭狼嚎一般的怪声,正像民谣所描述的那样: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而更为严重的残景在另一首民谣里留存至今:早为村庄夕沙压,大风起来不见家,爹死了娘嫁了,哥哥嫂嫂贼杀了,二亩半地沙压了……民谣给我们展示的是历史上沙尘暴肆虐后的景象,大风迫使无辜的农人背井离乡,亡命流浪……
1993年的5·5黑风暴,打击的目标明确而又狠毒,我们这代人已成为农业行档里的中坚力量,所以我们所受的心灵之痛也是剧烈的。为了向土地获取更大的利益,天然林、荒滩、沙丘在机械、畜力、人力的联合作战下,迅速变为一畴畴农田,一眼眼机井把水泥的吸管植入大地干瘦的胸膛。这块平原承受了从未有过的重负,被利益彰蔽了理智的人们在新垦的土地上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5月5日下午,大风掀天揭地而来,那些翻腾不息的风浪,呈现着阴森可怖的色彩,它的主色调无疑是灰暗和灰暗。我在新荒地上灌水,看着气势汹汹滚滚而来的蘑菇云手足无措。一个在沙漠腹地生存了三十多年的人,早已领教够了沙尘暴的雄劲霸道,我知道这样的风一旦走过我们的土地,那些刚刚萌发的幼苗定会迅速枯萎,整好了的土地将会变得凹凸不平。风还在遥远的西边张牙舞爪,我的头发就开始了纵情的舞蹈,这风一定不是张声张势的那种,我和妻子扛了锨准备走向临时搭建的茅棚。在我没有按计划到达之前,狂风早已笼盖了四野。
风毫不客气,简直不把我们当个东西。天霎时黑成了一个黑色的洞窟,在新垦的荒地上横冲直撞,我和妻并肩逆风而行,谁也看不见谁的模样,我们用锨巴作为链接试图在不分开的情况下走向茅棚,但我们到达的地方确远离了目的地。一颗大树碰在了我的额上,我们走进了幸存的一小片树林里。我们提高了嗓门相互通话,话语一出口,就被风老鹰叼小鸡一样叼跑了。我不知道我们的语言跟上风跑啥?它跑远了还是那句话吗?它为啥背离了主人随风而逝?在大自然的神威下,人是多么渺小,人是多么的不能自持和自控啊!我俩已失去了寻找目标的勇气,倚了沙枣树唯恐被大风吞了去。飞起的沙尘打在脸上,有了一种尖锐的力量,如针芒刺过。浓稠的沙尘让人无法舒畅地进行简单地呼吸。我们扶住大树,如揪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我和妻相倚而走,却无法进行语言上的抚慰和沟通,更没有了平时的戏谑和打逗,嘴里只徘徊着一句挣不出门坎的话:快停下来吧!风。风,快停下来!
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思已然脱离了对利益所报的希冀。我们的新荒地距家约有三十里地,孩子和老人的平安成了被困于大风中的人的最大悬念。他们可否在大风来临前安全回家?成了荒地上人们最牵肠挂肚的事。
大风依然雄劲,黑幕渐渐退去。持续三四十分种的黑暗,让我体会了漫长、无助、恐怖的滋味。这时候我看见同伴用自己的衣服包在驴头上,他与他的忠实伙伴——驴,经历了这场恐怖和黑暗。驴不吭一声,他也不吭一声,但驴和人心心相系,谁也没有背离谁乘风而去。人、牲畜从不同的地点向相同的地方汇聚,简易的茅棚变成了拓荒者共同的家。
所有的地上都飘扬着白色的旗帜,地膜成了这场风招摇的对象,看着乘风飙扬的地膜,我们的心痛楚无状——那些俏皮飞舞着的地膜是农人用血与汗换来的钱啊!钱是这样遭践的吗?你痛是你的痛,风不管这些,风照样刮,风按着它的计划,该撕谁的撕谁的,该扯谁的扯谁的,它把坑刮成了丘,把丘刮成了坑。田间的水渠被咬出了许多豁口。所有出土的瓜苗都变成了流泪的光杆司令。草本木本的残根遗须在风中呜呜地嚎哭,瑟瑟地颤抖。
这年的春夏之交,所有在外种荒地的人都阴着一脸云,好像谁估意恼怒了他。村里人勿忙地奔走在荒地和村庄之间,驴的蹄声回荡在三十里黄土大道上。打井投了巨资的人蔫成了茄子,眼珠子一转眼泪花就一闪一闪地亮。年终的收获自然远离了人们的想像,有些人陪了本,一个夏季碌奔忙换来的是一腔吐不出装不下的怨气。人们怨声载道,骂声震天:驴日的,天不养人了!我知道这样的灾难对一个农人的打击是残酷的,骂天骂地,日娘操老子都是舌头抵抵上腭,风该来时还来,该去时便去。风是天地之气,天情绪好的时候,我们便能享受清风徐来的快感,天的气不顺了,天就发怒,天之气一聚一出就变成了沙尘暴。沙尘暴是天地之怒气呵!当我们的欲望大于天地的赐予,当我们的贪婪超越了自然的能力,天地就会震怒,这是理之所然。谁说天地无情,天地如果无情,天就不行云布雨,地就不生花结实。青山绿水,麦秀豆香,鸟语花香、瓜熟果成……是天地化育之神功。
5·5黑风暴的残痛打击,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人们依然贪婪的拓展耕地,强逼土地获取收益。整个九十年代,人们在灾害打击的沮丧和获得收益的欣慰中痛并快乐着。沙尘暴的出现也越来越频繁,中央电视台的气象预报中常常出现一个叫作民勤的县名,沙尘暴的标示符号总是贴在她蝶形的版图上,像美女脸上突兀而出的紫斑,更似混世瘪三脸上残留的刀痕。民勤绿洲亟待治理,关井压田势在必行。封沙育林,种草禁牧,科学节水,成了红头文件中频频出现的词汇。极积的整治,不可能在短暂的时间里获得理想的进展。由来已久地榨取和索求让这片绿洲元气大伤,慢病快药显然是不合天理的行为,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的决策,需要在科学的实践中完善。
风蜷缩在它的巢窠里伺机而动。
2010年4月24日下午,一场多年不遇的沙尘暴在新疆的部分地区施足威风,然后扬鞭策马,横扫千里河西走廊,穿越民勤绿洲。风过处,天地顿时变得混沌不清,树木折断、电线受损,屋瓦树叶一样奋翅横飞,农田遭到严重破坏,设施农业损失惨重,这次沙尘暴引发了十多起重大火灾。田野上,林网上,电线上挂满了黑白两色长短不同的地膜,其状其景惨不忍睹,一个新的名词迸出多种媒体——特强沙尘暴。确乎,这次沙尘暴比我经历的任何一次都更凶猛,更强大,更让我恐怖。与十七年前的5·5黑风暴遥相呼应,给人们的心灵深处打上了一道永远拂之不去的烙印。央视在《烈火沙尘暴》的专题片的结束语中这样警示:不要认为沙尘暴只会发生在民勤,如果我们不采取科学应对措施,说不定沙尘暴哪天就会出现在我们的家门前。民勤不是民勤的民勤,民勤是甘肃的民勤,是中国的民勤,更是世界的民勤。
民勤环境亟待治理,每个有良知的地球人都有责任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中国的道学思想和中医理论告诉我们,大自然和人体都是一个平衡体,任何部位发生的疾患都会诱发更大的病痛出现,因之而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
风就握在我们手中,当我们因贪欲的驱使伸开了索取的大手,风就会逃出手掌横行肆虐,毫不留情,就会让我们的家园伤痕累累蒙受劫难。倘若我们以智慧的手段,勤勉地去整治,就会赎回地球家园一个蓝蓝的天空,绿绿的草地,清清的湖泊,爽爽的微风。那么沙尘暴这个可怕的词汇,就会复归为三个独立含义的汉字。那么草原不再哭泣,农田不再忧伤,河流不再悲涌,小鸟不再孤独……
当我坐在腾格里和巴丹吉林夹缝里撰写这篇文章时,心情是沉重的,郁闷的,一次一次的大风,给我留下的不光是伤痕,更重要的是思考。作为一个世代耕耘在这片土地上的农人,对愈来愈恶劣的环境不能不产生忧虑,我们还能坚持多久?我们的下一代能否居留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为谁坚守?我们坚守什么……?无穷无尽的问号在我脑子里奔突,我寻不到好的回复,安慰这些活蹦乱眺的问句,因为这些问题不是我能回答的。
我个人的意志和能力显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在愈来愈壮大的沙尘暴里,我只有踡缩只能叹息,只能面对灾难木然而立。一股庞大的热流正从四面八汇聚而来,来自网络、媒体的关怀与支持让我精神亢奋。几于疲软的信念,重新振作了起来。近年来,多种单位、团体、志愿者竞相在绿洲营造生态林,参与石羊河流域的综合治理。我顿时信心倍增,如果能长久不懈的坚持到底,我们的家园就不会因风而逝,我们的绿洲一定会载歌载舞,将和谐幸福进行到底!
我是农民。我却是风沙前线横刀立刀的尖兵。是沙尘暴中迎风而战的红柳、胡扬、沙枣、梭梭和毛条,是笈笈、是沙蓬、是固守家园的无名小草,是抵御沙尘暴的血肉盾牌。
我的族兄,著名作家唐达天的小说《沙尘暴》用细腻的笔触,以文学的形式为我们展示了一次次风沙对村庄的袭击和劫掠。那些已然离开的风,给他心灵留下了无尽的痛。他在南方湿润清新的工作室里,笔走风尘,带给人们多少的警示和思考,我在他的《沙尘暴》里逆风而行,寻到了自己风中的家园,也看到了那些在与风沙格斗的场景中渐渐苍老了的亲人的背影。我与我的父母都无法躲避的出现在《沙尘暴》里,我们坚韧却无奈,我们顽强却卑微。因为我们只是人微言轻的农民。
【 长按二维码 关注听雨楼 】
听雨楼微杂志 —— 让我们重读凉州词
微信号:tingyulou2266
总NO.34期 / 主编:秦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