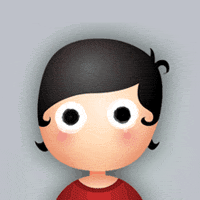【小说连载】王博艺 |《风尘》(二)
王博艺,男,汉族,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生,一九七三年平凉市四中高中毕业,甘肃镇原县平泉麻王人,农民。 甘肃作家协会会员,甘肃曲艺家协会会员,甘肃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甘肃文联原《文艺之窗》报记者,跻身全国百位农民作家行列。在省内外发表作品五十余万字,曾多次获甘肃省、市文学创作奖。著有长篇小说《社火》上、下部,《相逢在花城》,《野山》,《风尘》。出版《社火》上、下部,其中上部被中央文明办、、、、国家广电总局、中国作家协会等六部门列入《百位农民作家.百部农民作品》系列丛书,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野山》黄河出版集团阳光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长篇小说连载:《风尘》(二)
王博艺 著
第二章
洪河向东,向东,如蛇蜿蜒似地又流了十多年。
他又伫立在洪河岸边;伫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暮春一个阳光灿烂的正午。他不再是十多年前那个稚气十足的少年,而是一身书生气。
十多年前春日里的所见,简直是一场白日梦,是那么虚幻,那么扑朔,那么不可思义。他甚至怀疑那不是真实的存在,也许那时候自己神思恍惚,眼前出现的一切是幻景。
此刻,他的身旁停放着一辆独轮木小车,车上放着两个草綠色帆布包,方方正正如码着的砖块。这两个方方正正的草綠色帆布包,于别人也许不重要或微不足道,而于他意义很不同一般。包内装着他的精彩世界,装着他的精彩梦想;一个璀璨烂漫的精彩世界,一个五彩缤纷的精彩梦想。他在公社小镇下了客车,将精彩的世界和精彩的梦想放在独轮小木车上,推出五指塬的腹地,走下磨盘形状的南山,驻足在洪河此岸。
他推着独轮小木车,走在五指塬腹地的时候,脑屛幕不时地闪现出过去岁月的特写镜头;
雨云靉靆,宛若一嘟噜一嘟噜熟透了的硕大的黑葡萄,随时有垂落下来的危险。塬地上的一切黯然失色。霎时,雷电撕裂开乌黑的天幕,疾雨肆无忌惮地狂泻而下,整个塬地充斥着闹哄哄的雨声。白茫茫的雨帘里,村舍树木庄禾朦朦胧胧模模糊糊。道路泥泞,浑浊的流水齐着脚脖,小小的他‘扑通““扑嗵”向初级中学走去。雨鞭子恣意抽打着他,抽打得他的脸蛋麻辣辣疼,呼吸也有几分困难,短小的衣服粘贴着肌肤,浑身上下失去了感觉,自己似乎不属于自己了。他极其艰难地前行着……
老牛风在塬地吼叫着呼啸着,恣意地横冲直闯肆掠着,“嘎嚓”“嘎嚓”,说不清有多少树桠被摧折;“呼隆”,“呼隆”,不知有多少柴垛和草垛被掀翻了顶,在空中飞扬着。鹅毛大雪拧成一股股一团团,打着旋儿冲向塬地。平地上的积雪被老牛风刮得翻卷着,如海的波涛在汹涌,翻卷着汹涌着的雪浪,几乎填平了路壕。飓风沥雪冲打着小小的他,要睁大眼是十分困难的,他几乎闭着眼睑,凭着感觉朝前走,走向塬地的腹地——初级中学。老牛风越刮越猖獗,冲打得他几次栽倒在雪窝里,挣扎着爬起来。手指和脚趾最初那种钻心的酷冷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火辣辣的灼痛,传到心里也是火辣辣的灼痛感觉,他想纵声大哭,也许这样能抵御酷寒造成的这种灼痛,而鼻孔酸裂裂的痛,嘴唇僵硬的如石块,失去了血与肉做的本能。他的身后留下一行歪歪扭扭的雪窝,很快被翻卷着的雪浪掩没了。
他推着独轮小木车,向五指塬边走去,思绪如脱缰的野马,没有什么定式,没有什么桎梏,漫无边际地任意驰骋。一忽儿,他想到那个被树立为全国农民的“样板”,北京市大白楼生产队队长王国富,他——“小车不倒只管推”。那幅宣传画立时展现在他的眼前,王国富推着做工粗糙独轮小木车,他的脸孔也很粗糙,只有线条感,没有血肉感。王国富的小木车推的什么,我推的什么,相形之下,是一个绝妙讽刺。他向着蓝天纵声大笑,听见自己的笑声传得很远很远,飘向蓝天的深处,钻入脚下千米深的黄土层。这一刻,他一点也没想到自己的举动有些轻狂。他只想到自己既然立在这天地之间,就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就有自己存在的价值,自己属于自己。
“一鸣兄弟,回来了。”
金玉凤一边向他打招呼,一边舞蹈似地从小木桥走了过来。
郑一鸣沉浸在忘我的状态之中,没有听见金玉凤的热情问候。
“想什么想”金玉凤走下独木小桥,修竹似的腿一点也没打弯儿。她从来注重自己的体态体形,形成自然的习惯,看不出一点矫揉造作。
“老嫂子,你好!”
她并不老,是一个二十八岁的少妇,正处在女人成熟美的年龄。
洪河川的习俗,同辈男女之间,女人比男子年龄大数岁,在称呼前加一个“老”字,以表示尊敬之意,听着也有几分亲切。
“带回这么多的书。”金玉凤拍着独轮小木车上的帆布包,纤纤的手指犹如撑开着的花瓣,丹凤眼汪着生动迷人的光彩,
她的眼神色彩一直这么生动迷人。郑一鸣的心里说。
郑一鸣在泾水市就读初中和高中,三年多没回三姓庄,没想到风吹雨淋酷日灸烤,金玉凤的韵色仍然一点没减,风姿还是那么绰约,同样的生活条件和环境,她在同龄女性中就显得特别,也许是天生丽质。郑一鸣心里又想。
“读书好,有书读就好。做完活儿,读读书是再也好不过的,会有很好的心情。”
金玉凤知道郑一鸣高中毕业要回乡的,他的母亲王杰英早几天告诉过她。
郑一鸣不知道金玉凤是出于同情心,还是说他喜欢听的,不论出
自那一方面于他并不重要。出于礼节,他友好地向她笑笑。
“老嫂子,真能体谅人,谢谢。”
“叫新姐,别叫什么‘老’的,洪河川就这一点不好,人没老把人往老里叫。”
金玉凤过门那会儿,他叫她“新姐”,她扭动着好看的腰肢,
声音脆脆的甜甜的应着“哎——”,拖音好像飘着似的悦耳。
新姐,年轻,漂亮。他投其所好,又“嘻嘻”一笑。
“嘴唇抹油。回头见!”
金玉凤挥挥手,轻盈洒脱地走了。
他仿佛又看见了那只红狐,它蹲坐在圆月形状的冰块上旋转着……
那个初春日的正午,他要去看的戏,就是金玉凤主演的。那时候的金玉凤过门不久,是个谁见谁喜欢的漂亮新媳妇,男人的眼睛像锥子,往她苗条的身段和姣美的脸蛋上扎。与其说观众在看戏,不如说在看她。她是戏台上最靓丽的一道风景。她在戏台一亮相,观众的眼睛立时充满了灿烂的春光,脖颈伸得长长的,眼睛定定地如中魔似的。她一下场去,戏台頓时失去了色彩,甚至黯然下来。观众的兴致不再在戏台,尽管别的演员在倾心竭力的表演,他们不向台上望,颇有兴趣品评着金玉凤的唱腔和戏路。金玉凤是三姓庄自娱戏班的台柱,只因有了她,自娱戏班别开生面,不但享誉乡间,在公社小镇也有点名气。从前,这个戏班是清一色的男演员,表演水准平平,特别男装女扮,移步甩袖非男非女,唱腔像阉鸡啼叫。乡里人嘛,自娱就是自娱的水准,图个热闹也就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
郑一鸣推着独轮小木车走上了独木小桥。
桥面三寸多宽不甚规则,他推着独轮小木车不经意地辗过。他没看小桥一眼,直视着河的对岸。这一段河面非常平缓,如清亮亮的镜子,小木车压得独木桥不时地和河水亲吻着,似乎叙说着一个梦的话题。他的心里诗兴大发:
一个不变的话题
你叙说着
春来秋去
淘走多少梦想和诱惑
一个不变的话题
你叙说着
花开花落
淘走多少悲欢离合
他常常自已被自已激动、兴奋,激动得无法表达,兴奋得超然物外。
他坚信不疑,自已推着的精彩世界和梦想,总有一日会变为精彩辉煌的“洪河梦” ……
到了彼岸,他望着东流而去的洪河,欲向它说什么而又没说,只觉的身心生出一种无穷的力量,觉得自已一点也不渺小,似乎看见未来的自已很伟岸。神经质。他暗自发笑自已狂傲得挺可以。这是一个扼杀个人主义的时代,换而言之,就是戕杀人的个性。不要说张扬个性,你偶然流露出那么一点点,草木皆兵共诛之。而他天生个性特强,越是遭压抑激情越是如火山般喷发,从初级小学到高中毕业,他的操
行语总少不了“爱出风头”“好个人表现”云云······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