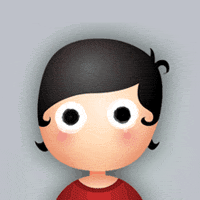蒋绍愚先生:谈谈博士生的培养
谈谈博士生的培养
蒋绍愚
蒋绍愚先生
蒋绍愚先生,1940年1月出生于上海,籍贯浙江富阳。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教龄达50余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文系副主任,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主任。现受聘为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分别于1992年、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和国家级“教学名师”。主要著作有《古汉语词汇纲要》《唐诗语言研究》《近代汉语研究概要》《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统稿)。此外,还先后主编《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蒋绍愚、曹广顺主编)等。发表百多篇论文,部分论文汇集为两本论文集:《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续集》。
摘要:博士生的培养目标是为他们今后的科研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果只注意博士论文的撰写而忽视了全面的基础训练,那是舍本逐末。博士生的学习和培养,面要广一点,眼界要开阔一点。本文根据通过作者对汉语史博士生的培养的体会说明上述问题。
关键词:博士生的培养;汉语史;文献资料;学科领域;理论方法
我从1994年开始招收博士生,至今已17年了。对于博士生的培养,我有一些体会,在这里简单地谈一谈。博士生的培养,一个首要的问题是博士生培养的目标。博士生培养的目标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是使他们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熟悉本专业相关的理论,具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为他们以后的科研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博士生四年的学习时间里,一、二年级应该学习各种必修和选修的课程,在导师指导下,广泛地阅读,深入地思考,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开阔眼界,培养从事学术研究所必需的学术眼光和研究能力。三、四年级重点转到写博士论文,通过论文的写作,加深对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理解,进一步提高研究能力。不论是博士生本人还是博士生导师,都很看重博士论文。确实,博士论文是博士阶段的最终成果,是博士生培养成果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应该重视的。但是,有的博士生为了写好论文,一入学就把全部精力用来写论文,把注意力局限在只和自己的论文有关的范围内,这样就不对了。如果导师鼓励学生这样做,那就是对学生的误导。应该看到,写博士论文是培养的手段,不是培养的目的。如果四年时间只用于写一篇论文,忽视了全面的基本训练,那是舍本逐末。这不是培养博士生的正确途径。
博士生的学习总共只有三、四年的时间,又要打基础,又要写论文,时间确实是很紧的。所以,博士生的学习和培养必须有所侧重。首先要侧重于他的专业方向,比如,或是汉语史,或是现代汉语等。在大的专业方向范围内还要有所侧重,比如,汉语史方向的博士生还要确定重点是音韵还是语法、词汇,是上古还是中古、近代。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另一方面,当前学科发展的总趋势是专业范围的扩展,以及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如果确定了一个专业方向,就画地为牢,除此以外的就一概不问,这样,不但对将来的发展不利,就是本专业也难以学好。所以,博士生学习和培养的面又不能太窄。针对目前的情况,我认为应该强调的是:博士生的学习和培养,面要广一点,眼界要开阔一点。下面根据我从事的汉语史专业谈一点自己的体会。
一、要重视汉语史研究的各类文献资料
汉语史研究的是汉语发展的历史。这个学科进行研究的基本依据是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语言材料。语言材料既是汉语史研究的出发点,又是检验汉语史研究成果的最重要的标准。那么,有哪些汉语史研究的语言材料呢?这范围是十分广泛的。不仅有传世文献,而且有出土文献,不仅有中土文献,而且有汉译佛典和域外文献。汉语史的研究者必须熟悉这些语料,正确理解这些语料。下面分别谈一谈。
(1)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
传世文献历来都比较重视,这确实是汉语史研究的基本资料。但是,从20世纪以来,大量的出土文献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注意。甲骨文、金文、敦煌文书(敦煌文书不是出土文献,但也不是传世文献,所以放在这里一起谈)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就是20世纪70年代至今新出土的马王堆帛书、郭店竹简、清华简等,其重要性也是举世公认的。就汉语史的研究来说,这些出土文献提供了很多原先在传世文献中看不到的语言资料。今天我们研究汉语史,绝不能无视这些资料。举个例子。《论语》是研究先秦语言的重要资料。传世文献中,有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这两个本子就不完全相同。20世纪以后,在敦煌文书中又发现很多《论语》郑玄注的抄本(残),还发现了定州汉中山怀王墓中的《论语》,和传世文献《论语》的差别更大。据北京大学博士生曹银晶的研究,《论语》中语气词“也已矣”三字连用,在阮元本《论语》里共出现8例:
1)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泰伯》)
2)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泰伯》)
3)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子罕》)
4)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先进》)
5)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颜渊》)
6)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颜渊》)
7)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卫灵公》)
8)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子张》)
只有(3)、(4)、(7)三例的文字见于定州本,原文各作:
3a)说而不择,从而不改,吾无如之何矣。(《子罕》)
4a)何伤?亦各言其志也。……也。(《先进》)
7a)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卫灵公》)
上博简中,单个语气词共有5种:也103、矣36、乎19、与5、哉2,占整个语气词用例的95%左右;语气词连用使用情况,共有4种:也与4、也夫2、也乎2、也已1,占整个语气词用例的5%左右。不见“也巳矣”连用。上述阮元本《论语》8个“也已矣”在敦煌写本里作“也”、“矣”、“已矣”或“也已矣”等多种情况,而作“也已矣”者较多。到唐石经中八处均作“也已矣”。如果我们单凭何晏《论语集解》,就会认为《论语》中语气词“也已矣”连用是常见的现象,并由此推论认定先秦时三个语气词连用很常见。但是,如果把出土文献资料材料综合起来考察,那么何晏《论语集解》中的八处“也已矣”连用究竟是不是先秦的语言现象还值得怀疑。仅此一例就可以看到,出土文献对汉语史研究多么重要。
(2)中土文献和汉译佛典
汉语史研究的是汉语的发展。但汉语不是孤立地发展的,在汉语发展的漫长历史中,汉语多次与邻近的其他语言接触,受其他语言的影响。其中很重要的一次,就是东汉以后传入中国,有不少“胡僧”把大量佛典(原文是梵文或巴利文或中亚语言)译成中文,从而对汉语产生影响。所以,这些汉译佛典也是研究汉语史必须重视的资料。也举一个例子:汉语自古就可以把“已/竟/迄/毕”放在动词或动词词组后面,表示动作完成。但“竟/迄/毕”用得比较多,“已”用得比较少。而且,这些词的用法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完”,只能用在持续动词后面,如“食已”、“读竟”等,而不能用在瞬间动词后面,不能说“觉已”、“死竟”等。但在汉魏六朝的汉译佛典却和中土文献很不一样。据蒋绍愚(2001)统计,在汉译佛典中“已”用得很多,而中土文献中是0:
而且,汉译佛典中“已”可以用在瞬间动词后面,如:
1)觉已惊怖,向王说之。(贤一2)
2)到竹林已,问诸比丘。(贤四23)
3)值一木工口衔斵斤,褰衣垂越。时檀腻羁问彼人曰:“何处可渡?”应声答处,其口开已,斵斤堕水。(贤十一53)
4)驼既死已,即剥其皮。(百42)
据辛岛静志(2000)研究,这种“已”是一种时态助词,和梵文原文有关,相当于梵文的绝对分词。在梵文里,绝对分词一般表示同一行为者所做的两个行为的第一个(“……了以后”),可以用在瞬间动词后面。汉译佛典中的“瞬间动词+已”是受梵文影响而产生的。这说明佛典翻译对汉语语法发展的影响。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汉译佛典对汉语史研究的重要性。
(3)域外资料
有时,汉语史的一些重要现象在汉语中不见踪迹,而在域外资料中却有反映。如王力(1958)说:上古声母“云”和“余”的分别,在现代汉语诸方言中都不存在,但直到现在还保留在越南的汉语借词(所谓“汉越语”)里;云母是v,余母是ʑ(写作d),例如“王”作voung,“阳”作duong,“云”作van,“余”作du,“为”作vi,“惟”作duy等。
有时,汉语史的一些重要变化,首先记录的不是汉语的资料,而是域外资料。如杨耐思(1981)指出:最早反映北方话中-m尾已并入-n尾的,是崔世珍的《四声通解》(1517)。《四声通解·凡例》:“诸韵终声L、O、□(-n、-N、-m)之呼,初不相混,而直以侵覃盐合口终声汉俗皆呼为L,故真与侵、删与覃、先与盐之音多相混矣。”又如,明清时期韩国、日本的一些汉语教科书,19世纪西方传教士的一些汉语教科书和汉语翻译著作,都反映当时汉语的面貌。现在有一些学者已经或正在做相关的研究。可见,域外资料对汉语史研究也很重要。
这里附带谈一个问题:怎样收集和使用语料?汉语史的研究,离不开语料的收集。以前研究汉语史,语料是要研究者长年累月地积累起来的。现在有了电脑和语料库,收集和检索语料容易得多了。这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如果只依赖电脑和语料库,而不用自己的头脑对检索的结果加以理解和分析,完全用电脑代替了人脑,这就可能导致错误,好事也就变成了坏事。这是必须引起注意的。例如,在研究汉语史上连词的发展时,有人用电脑检索得到唐代文献中一些“N+和+N”的例句,就认为连词“和”在唐代已经出现。这里仅举一例:
1)白头病叟泣且言,禄山未乱入梨园。能弹琵琶和法曲,多在华清随至尊。(白居易《江南遇天宝乐叟》)
是不是根据“和”前后都是名词,就能够确定它是连词呢?这样太轻率了。在检索到这个例句以后,首先应该理解这个句子的意思。这个句子能理解为“能弹琵琶和法曲这两样东西”吗?这就先要了解什么是“法曲”。“法曲”是唐代的一种乐曲。而“琵琶”是一种乐器。这两者是不能用连词“和”加以并列的,正如我们不能说“能弹钢琴和交响乐”。那么,“和”字应该怎样理解呢?下面的文句会对我们有所帮助:
白居易《法曲-美列圣,正华声也》:“乃知法曲本华风。”
元稹《立部伎》:“宋沇尝传天宝季,法曲胡音忽相和。”
显然,“能弹琵琶和法曲”的“和”与“法曲胡音忽相和”的“和”意思是一样的,是个动词,“协和、协调”的意思。“琵琶”是一种来自西域的乐器,“法曲”本是“华风”,“这个乐叟能弹琵琶来与法曲相协和”,这才是对这个句子的正确理解。这样理解,就不会把这个句子当作连词“和”在唐代已经出现的根据了。
二、汉语史研究的领域不要分得太细
上面说过,汉语史的博士生还要分成不同的专业方向,如音韵、语法、词汇,以及上古、中古、近代。这是必要的。但不要分得太细,因为这些领域彼此是有联系的。如果能侧重于某一个领域,而对其他领域也有所了解,这样视野就比较广阔,即使是研究本领域内的某个问题,也可以顾及相关的领域,因而研究得比较深入。
(1)要注意语音、语法、词汇之间的关系
以往把词汇和语法看成两个不同的领域,实际上,词汇和语法是有密切关系的。人们在用语言来表达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时,有时把某一语义要素作为词的语义成分包含在词中,有时把这一语义要素作为单独的一个词出现在语法组合之中。词的不同语义构成会影响句子的语法组合。胡敕瑞(2005、2009)指出:从上古到中古,有一种“从隐含到呈现”的现象,上古主体与动作融合(崩=山+崩),修饰成分与中心成分融合(金=黄+金)、对象与动作融合(启=开+门)、动作与结果融合(破=打+破)。这四类融合也可理解为四类隐含,即主体隐含于动作,修饰成分隐含于中心成分、对象隐含于动作(或动作隐含于对象)、动作隐含于结果。中古四类“隐含”纷纷“呈现”:主体从动作中呈现出来(崩→山崩)、修饰成分从中心成分中呈现出来(金→黄金)、对象从动作(或动作从对象)中呈现出来(启→开门)、动作从结果中呈现出来(破→打破)。呈现的结果会对句法有影响,如下面两句话,原来“启”的宾语是“之”,“唾”的宾语是“其面”;后来“启”隐含的对象(户)、“唾”隐含的对象(口水)呈现出来作为它们的宾语,它们原来的宾语就只能改变位置,作为介词宾语出现在句子中。如:
1)夫人将启之。(左传·隐公元年)——后代要说成“夫人将为之启户”。
2)老妇必唾其面。(战国策·赵策)——后代要说成“老妇必对其面唾口水”。
原来有一种说法:“句法无涉语音”(phonology-freesyntax)。但冯胜利(2009)不同意这种说法。他指出:韵律制约词法和句法。比如汉语“被”字句在东汉以前不能出现施动者:
1)万乘之国被围于赵。(战国策·齐策六)
直到东汉末期,才出现施动者:
2)臣被尚书召问。(蔡邕《被收时表》)
这是为什么?他认为先秦的“被+V”(如“被围”、“被困”等)都是标准的双音节韵律词,中间不允许插入东西。东汉以后随着汉语的复音化,单音节的“V”变成了“VV”,从而也把“被V”的双音节模式拉长为三音节的[被VV]。到了东汉《论衡》时代才出现“被侮辱”、、“被毁谤”一类三个音节的结构。三个音节[被VV]是一个短语,自然允许双音节的施动者插入“被”和后面的双音节动词之间。在今天的被字句里,如果动词挂单,施动者仍然允许容置入其中:
3)*悟空常被师傅批。
4)悟空常被师傅批评。
可见语音对语法有影响。语音和词义的关系很密切,“音义关系”是中国传统语言学讨论的一个老问题,此处从略。
(2)要重视上古、中古、近代之间的联系
为了显示汉语发展的阶段性,也为了研究的方便,把汉语史划分成若干阶段时期是必要的。但是,汉语的发展毕竟是一个整体,要研究某一个时期中的某种语言现象,往往需要联系到其前和其后的有关问题。如果把自己的研究局限于某一个时期,而对别的时期不闻不问,那是会影响研究的深度的。也举一个例子。在中古的汉译佛典中,可以见到这样的句式:
1)佛告拘怜:尔时忍辱道人者,我身是也。恶生王者,拘怜是也。(中本起经·卷上)
2)佛告比丘:尔时天帝者,大迦叶是也。文陀竭王者,则是吾身。(中本起经·卷下)
3)佛告诸比丘:尔时高行梵志,则吾身是也;五百弟子,今若曹是也;时谏师者,舍利弗是也。(中本起经·卷下)
这种“NP1,NP2+是也”句式该怎样分析?是怎样产生的?这似乎是中古汉语研究的课题。但是,先秦文献中的“NP1,NP2+是也”也有不少,如:
4)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孟子·梁惠王下)
5)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荀子·不苟)
6)凡物不并盛,阴阳是也;理相夺予,威德是也。(韩非子·解老)
元明时期也有“NP1,NP2+是也”:
7)自家不是别,乃是万俟丞相府中堂候官的是也。(荆钗记19)
8)某乃宋江便是。(元曲选·李逵负荆·2)
9)老夫王员外便是。(元刊杂剧小张屠楔子)
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NP1,NP2+是也”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它们的来源是否一样?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这就不是局限于汉语史的一个时期所能回答的了,而必须把汉语史的不同时期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所以,我们反复强调,博士生学习和研究的面要宽一点。
三、要注意现代汉语和现代方言的研究成果
,汉语史、现代汉语(包括现代汉语方言)同属于“汉语言文字”这个二级学科。但实际上,汉语史和现代汉语的博士生的导师是分开的,课程也大部分是分开的。这样做有它的好处:汉语史和现代汉语分开,各自可以研究得更深入一点。但也有一个明显的弊病:汉语史和现代汉语本来是汉语一脉相承的历史发展,现在把它们割断了。补救的办法是:在汉语史和现代汉语各自侧重的前提下,尽量注意两者的联系,学习汉语史的要注意现代汉语和现代方言的研究成果,同样学习现代汉语的要注意汉语史的研究成果。现在,有些大学的博士生选课的面比较宽,汉语史的博士生也选一些现代汉语的课,现代汉语的博士生也选一些汉语史的课,这是一种良好的、值得鼓励的趋势。
(1)学习研究现代汉语的成果以及理论、方法
汉语史和现代汉语都是对汉语的研究,但两者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方法有较大的不同。现代汉语研究的系统性较强,研究方法比较多样,理论思考比较深入,这是值得汉语史的博士生学习的。实际上,目前汉语史研究中有不少问题都是借鉴了现代汉语研究的成果,比如,汉语史上词类的划分,基本上就是采取了现代汉语词类划分的框架;汉语史中同义词的研究,也采用了现代汉语同义词研究的基本原则。所以,对汉语史博士生来说,了解和借鉴现代汉语研究的成果,是十分必要的。
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现代汉语研究者的理论意识。下面是陆俭明、沈阳《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第三讲到第十四讲的标题:
结构理论与结构层次分析
变换理论与句式变换分析
特征理论与语义特征分析
配价理论与配价结构分析
空语类理论与空语类分析
移位理论与成分移位分析
约束理论与语义所指分析
指向理论与语义指向分析
范畴理论与语义范畴分析
认知理论与语言认知分析
语用理论与语言运用分析
类型理论与语言类型分析
《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是一本面向大学文理科本科生的通识课教材,为什么要给学生讲这些当代语言学的理论呢?这是因为,这些当代语言学的理论在现代汉语研究中用得很普遍,要懂得现代汉语研究的最新进展和最新成果,就不能不懂一点这些当代语言学的理论。实际上,现代汉语研究近20年来的进展,很大程度上是运用这些理论来研究现代汉语的结果。现代汉语研究者的这种理论意识是很值得我们汉语史的研究者学习的。特别是那些现代汉语研究的优秀成果,更向我们展示了如何把理论和现代汉语的语言事实结合起来,在研究方法上给我们以启示。这对我们更是十分有帮助的。
当然,对待理论要有正确的态度,这在下面将会讲到。而且,虽然历史上的汉语和现代汉语都是汉语,但两者还是有差别的。除了语音、语法、词汇的差别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别:现代汉语是活的语言,是大家每天都在用的;历史上的汉语史是死的语言,主要存在于文献资料上。所以,现代汉语研究的成果和方法不能简单地搬到汉语史研究上。这也是必须注意的。
(2)把现代汉语方言和汉语史结合起来
研究汉语方言的研究是现代汉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和汉语史的研究有很密切的关系。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讲到建立汉语史的根据时说:“首先要说,现代活生生的口语就是汉语史的最好的根据。现代汉语的方言是复杂的;正是由于方言的复杂,更有足够的语言事实来证明汉语发展的过程。……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对于汉语史的建立,是能起非常重大的作用的。”
汉语方言在语音方面对汉语历史音韵研究有重要作用,这已为大家熟知,这里不必多说。在语法和词汇方面情形是一样的。桥本万太郎(1985)提出“语言发展波浪说”,认为语言是从中心地区一波一波地向四面扩散,今天汉语方言中词汇、语法的地域分布就是汉语历史发展在时间上的顺序的投影。比如,在北方方言中叫“锅”,在吴方言中叫“镬”,在闽方言中叫“鼎”,这正好反映了汉语历史上“鼎——镬——锅”的发展顺序。北方方言中说“比天高”,粤方言中说“高过天”,这也反映历史上“高于天——比天高”的语序变化。当然,实际情况会复杂得多,但从总体上看,他所说的时间和空间的关系还是有道理的。
以往的汉语方言研究,比较注重于记录和描写。近来已经在此基础上大大跨进了一步,注意方言中历史层次的研究。要研究历史层次,当然首先要对汉语史上不同历史层面的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反过来说,如果能把诸方言的历史层次都研究得比较清楚,那就为汉语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活生生的口语材料。这些材料可能是对历史文献的印证,也可能是在历史文献中看不到的。以前研究汉语史的人对方言注意得不够,今后如果把汉语史和汉语方言结合起来研究,应该是大有可为的。
(3)为现代汉语的语言现象寻找历史来源
上面说汉语史的研究应该向现代汉语(包括汉语方言)的研究学习,下面说事情的另一方面:汉语史的研究反过来也有助于现代汉语的研究。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为什么只能说“他是小王的老师”,不能说“他是小王的教师”?因为“老师”是二价名词,所以可以有两个论元“他”和“小王”。“教师”是一价名词,所以只能有一个论元“他”。这当然是正确的回答。
但是,如果进一步问:“老师”和“教师”指的是同一种人,为什么一个是二价,一个是一价?这个问题,无法从现代汉语的平面上回答,而必须从汉语史的研究找答案。从汉语史的角度看,“老师”和“教师”虽然都有一个语素“师”,但是这两个“师”实际上是不同的。“老师”古代就称“师”,是传道授业的人,所以总是和被传授的人分不开的。《荀子·修身》:“师者,所以正礼也。”《礼记·文王世子》:“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老师”最早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这个“老”是“年老”的意思。现代汉语中“老”是词头,但“师”仍是这个“师”,所以“老师”是二价名词,可以而且常常说“X是Y的老师”。“教师”的“师”是表示一类有某种技能的人,如古代有“渔师”、“罟师”,现代有“厨师”。左思《吴都赋》:“篙工楫师”吕向注:“工,谓所善,师,谓所长。皆使其驾行舟者。”“教师”在元曲中可以见到:张国宾《罗李郎》3:“人都道你是教师,人都道你是浪子。”意思是教习歌舞技艺的人,到清代才指传授知识的人。因为和“罟师”、“厨师”一样是一种职业,所以是一价名词,可以把他和就职的单位联系起来,比如说“他是全聚德的厨师”,“他是北大附中的教师”,但不能说“X是Y的教师”从这个例子不但可以看到汉语史和现代汉语的联系,而且可以看到词汇和语法的联系。
第二个例子。有些现代汉语的复合词,被认为其构词方式是无法分析的。如“卧病”,意思是“因病而卧床”,但“卧”在前,“病”在后,和汉语的语序相反,是一种无法解释的构词方式。确实,从现代汉语的角度来看,“卧病”一词中两个语素的这种顺序在构成句子的语序中是找不到的。但是,“今天的词法曾是昨天的句法。”(T.Givon)这种语序在汉语史中是否能找到呢?我们找到了这样的句子:“诘朝尔射死艺。”(左传·成公十六年)“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韩愈《进学解》)。“死艺”“号寒”“啼饥”的意思都是“因~而V”,但语序都是“V+~”。在古汉语中,“卧病”或“卧疾”都是词组,其语序也是也是“V+~”:“卧病同淮阳,宰邑旷武城。”(谢灵运《命学士讲书》),“卧疾丰暇豫,翰墨时间作。”(谢灵运《斋中读书》),“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白居易《琵琶行》)。古汉语的这种语序在现代汉语中消失了,但“卧病”凝固成一个词在现代汉语中保存下来。
如果只看现代汉语的平面,“卧病”的构词方式确实是不好解释的。但如果把汉语史联系起来考察,就不但能解释这种构词的由来,而且可以看到句法和词法之间的历史上的联系。
现代汉语是汉语历史发展所形成的,现代汉语的很多现象都应该能在历史上说明其源头和发展过程。但目前汉语史的研究和现代汉语的研究有点割裂,研究汉语史的往往只管到到清代为止,研究现代汉语的一般不向上追溯。如果能把上下打通,这将是汉语研究的重大进展。在这方面,我寄希望于年轻的学者。
四、了解当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
上面已经说过,研究汉语史要重视当代语言学的各种理论。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语法化理论、语言接触理论、语言类型学理论、认知语言学理论等,对汉语研究的深入有很大的作用。这在现代汉语领域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汉语史研究中也有反映。当然,对这些理论要学得好,用得好,不是轻而易举的。这里有一个态度问题。如果不对汉语的材料做深入的分析研究,而只是把这些理论当作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用汉语的材料去迁就这些理论,这当然是无益而有害的。只有把汉语的材料作为研究的基础,用这些理论来观察、分析汉语的语言事实,解决汉语研究的问题,并且根据汉语的语言事实来对这些理论提出自己的看法,补充、修正这些理论观点,或者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有利于汉语研究和理论研究的深入。
对于汉语史的研究来说,语法化理论大家已经很熟悉,这里不再多谈。下面举例谈谈语言接触理论,语言类型学理论、认知语言学理论在汉语史研究中的运用。
(1)语言接触理论
在汉语发展过程中有过多次语言接触。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东汉时传入中国,在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翻译了大量佛典。这虽然不是操两种语言的人民直接的接触,但对汉语的影响是很大的。这在上面已举例谈过。另一次是从南北朝到辽金元时期,汉人和北方的阿尔泰民族频繁接触,形成了“汉儿言语”。特别是元朝蒙古入主中国时期,形成了“蒙式汉语”。比如下列句子,显然与通常的汉语有别,有蒙语语法的影响:
1)身体头发皮肤从父母生的,好生爱惜者,休教损伤者,么道,阿的是为头儿合行的勾当有。(孝经直解)
2)刘斌小名的汉儿人,诈称“廉访司奏差”么道,……杖子里敲着呵,怎生?(元典章·刑部十四)
3)这帖木儿,成都府廉访司官人有。(元典章·刑部九)
4)命不快上遭逢着这火醉婆娘。(马致远《陈抟高卧·4》)
5)女婿行但惉惹,六亲每早是说,又道是丈夫行亲热,爷娘行特地心别。(关汉卿《拜月亭·3》
但是,在元代,蒙语对汉语的影响究竟有多深?影响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对这种“蒙式汉语”的性质究竟怎么看?对这些问题还存在不同认识。有的认为“蒙式汉语”是一种皮钦语,有的认为“蒙式汉语”只是一种中介语。有的认为“蒙式汉语”是元代较普遍地使用的,有的认为只限于当时的官吏(特别是高级官吏)使用“蒙式汉语”,一般百姓的语言中没有出现特殊的语言现象。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继续对这些特殊语言现象作深入研究外,还需要对语言接触的理论有正确的认识,用语言接触的理论来观察这些语言现象。
(2)语言类型学理论
语言类型学发展得很快,在汉语研究中也运用得越来越广。类型学与历史语法学结合,“往往能向我们提示,什么样的演变是极为常见的,什么样的一般是不大可能的,什么样的演变常常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发生等等,因此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具体语言里某个特定形式演变的模式、路径和过程。”(张敏2003)
现在有不少文章,在研究了汉语史上某种演变趋势之后,引用语言类型学研究的结论,来说明这种演变趋势不仅在汉语中有,而且在其他语言中也有。这种做法可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但更值得提倡的是用类型学的理论和成果来解决汉语史研究中的问题。
例如:古代汉语中放在定语和中心语之间的“之”,其来源是什么?有三种看法:(1)来自指示代词“之”。(2)来自动词“之”。(3)是原生的。张敏(2003)首先对上古汉语的材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证明定语标记“之”是来自指示代词“之”的;并且运用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成果,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他把“之”这类定语标记写作AM,考察它在各种语言中的来源。各种语言中的AM有来自体词性成分(包括名词,体词性代词等)的,也有来自非体词性成分(包括动词、副词、介词等)的,但其结构构型有所不同:
第一,一些语言中的AM来自表位移关系的介词(at,from,for/to),如英语的“The Bishop of Rome”,of来自中古英语的of,意为from。法语、德语和其他几种语言的AM和英语的of相同原本都是from之义。但其结构构型均为“N2[AM+N1]”(中心语在前,定语在后),和汉语的构型“N1[之+N2]”(中心语在后,定语在前)不合。
第二,AM来自起复指作用的代词,这在世界许多语言里都有体现。如英语、德语、荷兰语、Afrikaans语、supyire语、诸南岛语言等。英语的’s和his不无关系。其构型为[A+(AM+B)],与汉语“N1[之+N2]”相同。这种语言类型学的考察是一个有力的旁证,说明汉语的定语标记“之”是来自指示代词“之”。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如果把类型学理论和汉语史材料的分析结合起来,可以解决汉语史的一些疑难问题。
(3)认知语言学理论
有一些问题,仅仅从语言内部无法找到答案,而需要从认知的角度来解决。例如,汉语在泛指方向时,基本上只用“东西”,而不用“南北”。在老舍的《四世同堂》中,“东V西V”很多,如:
东转西转、东扫西射、东倒西歪、东拼西凑、东张西望、东瞧西望、东扫西瞧、东想想西想想、东张张西望望、东打听西问问、东瞧瞧西看看、东晃一下西晃一下、东扑一下西扑一下、东一块西一块、东一束西一根、东一把西一把、东一脚西一脚、东一句西一句、你说东他说西。而“南V北V”等只有很少几个,如:南来北往、南征北战、山南海北、走南闯北。
现代如此,古代也如此。先秦和西汉前期的传世文献中,“东——西”泛指方位多次。如:
1)八、十九十者东行,西行者弗敢过;西行,东行者弗敢过。(礼记·祭义)
2)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周易·既济)
“南北”泛指方向仅一次:
1)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淮南子·说林)
为什么华夏民族自古就把“东/西”看作基本的方向呢?蒋绍愚(2007)认为有三点原因:第一,日月江河运行的方向。日出东方,日落西方,这是人们最容易感知的方位。但这是全人类共同的,仅仅根据这一点,不足以说明为什么有的语言以“东/西”为基本方位,有的不是。应该说“日出东方,日落西方”这一因素在有的民族的认知中由于其他因素而突显,在有的民族的认知中由于其他因素而减弱。在华夏民族的认知中是什么因素使之突显呢?是河流的方向。太阳从东向西,河流从西向东,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使华夏民族自古就把“东西”作为基本的方位。
第二,古代居住的方式。考古发掘的今甘肃秦安大地湾乙址的居住遗址,以901号大型房址为中心,南面有许多大小房屋,都是坐南向北,面对901号房址。每一小区以一座较大房址为区内中心,都是东西排列。(见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地区考古略说》)这种居住方式,使人们觉得东邻、西邻比南邻、北邻更为亲近。所以,先秦文献中有“东邻”、“西邻”而没有“南邻、北邻”。
第三,。周秦是华夏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周和秦原来都是僻居西隅的小国,后来逐渐向东方发展。,“东—西”远比“南—北”重要。,“关东、关西”、“山东、山西”常见,而“关南、关北”、“山南、山北”不见。
“东南西北”是四个并列的方位词,但在华夏民族的潜意识里,“东西”比“南北”重要。这在人们的语言运用中,古今都是高度一致的,但人们却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可以称为“集体无意识”。如果我们深入研究,可以通过语言事实挖掘它背后的“集体无意识”。这也是汉语史研究应当担负的任务之一。
参考文献:
[1]曹银晶.谈《论语》句末语气词“也已矣”早期的面貌[Z].待刊.
[2]冯胜利.论汉语韵律的形态功能与句法演变的历史分期[J].历史语言学集刊(2),2009.
[3]胡敕瑞.从隐含到呈现(上)[J].语言学论丛(31),2005.
[4]胡赖瑞.从隐含到呈现(下)[J].语言学论丛(38),2009.
[5]蒋绍愚.《世说新语》、《齐民要术》、《洛阳伽蓝记》、《贤愚经》、《百喻经》中的“已”、“竟”、“讫”、“毕”[J].语言研究,2001(1).
[6]蒋绍愚.东西南北[A]//语苑撷英(二)[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
[7]陆俭明,沈阳.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8]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M].余志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9]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10]辛岛静志.汉译佛典的语言研究[A]//《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1]杨耐思.近代汉语-m的转化[J].语言学论丛(7),1981.
[12]张敏.从类型学看上古汉语定语标记“之”语法化的来源[A]//语法化与语法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本文原载《中国大学教学》20112年第1期)
编辑:南客子
长按下方指纹识别二维码可以关注我们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