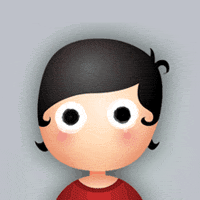付兴奎 | 最忆是柴禾之拉柴记【荐读】
最忆是柴火 之
拉柴记
文 / 付兴奎
村里的人把用来烧火的木头叫硬柴。在枯草都稀奇的年代,树木更是少得可怜,没办法,大家只好三五个一帮去后山里伐木烧。
那年正月,父兄们组成的拉柴队伍就是在一场大雪后进山的。漫天的大雪把世界涂成了一张硕大的白纸,小如飞蚊的父兄在铺满积雪的土路上举步维艰。过日子心劲十足的父亲显然已经没有了壮年时候的力气,不到二十岁的哥一身嫩骨更是不堪长途奔袭。三五十公里之后,大家浑身上下内内外外湿成了一片。冷风袭来,汗水成冰,原本暖和轻柔的衣服,立即变得坚硬和沉重起来,等到在山洼里找到歇脚的地方,差不多已经是掌灯时分了。父亲向主家要了一壶开水,然后拿出母亲做的窝头往水里一泡,一顿饭就算过了。
山里人实在,炕烧得扎实,但谁也不敢因此贪睡。摇摇晃晃之中,几个人一走又是大半天。第二天晌午,堂兄指着眼前深沟里一窝子树对父亲说,咱就在这儿吧。
结束了单调的走路,哥一下来了精神,他从架子车上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大板斧,瞅准近旁的一棵树就往下砍。三斧子过后,哥力气不足的弱势马上暴露出来了,刚才的腿疼脚疼很快变成了手疼胳膊疼。父亲则不紧不慢,从上往下转着了一遍,除了在沟底里发现几棵被风吹折的树之外,在那些便于砍伐的树干上做了记号。看上去身体并不魁伟的堂兄是个干农活的好手,不管什么样的树只要到了他的手里,十来斧子问题就解决了。
同样是木材,有些天生就是烧柴禾用的,有的还可以做家具。桦树肯着,榛子树耐烧,漆树上的漆粘到身上特别痒等等。拉木头的人似乎不在乎这些,什么树顺手砍什么。父兄们一边砍,一边抗,等到木头装好,差不多已经是晚上了。
厚腾腾的积雪覆盖了周围的一切,即便是到了晚上也没有黑暗的感觉。月光下的山川静得让人恐惧,走很久才能听到一两声犬吠。晚上看不见白天的脚窝,每走一步都如临深渊,没办法,拉柴的人只好找有人家的山窝窝住下,第二天再赶路。
白天出门时带的干粮和窝头,很快就吃完了。又累又饿的他们只好沿路讨买,那些山里人其实一点也不宽裕,问来问去,只有一升黑豆,他们只好花五毛钱买来炒了吃。
没有电话的年代,主要凭经验来估摸,第四天早上,母亲打发我和姐去接父亲他们,我们的目的很简单,一是看哥哥们有没有在山里找下什么可吃的干果,再就是能不能剥几张大点的桦树皮。估摸着他们快回来的时候,我们差不多二十分钟就跑到门前的土台台上瞭望一次,结果连父亲他们的影子都看不到。没办法,我们只好沿路去迎接接他们。在离家十五里左右的地方发现了拉柴的车子。满头大汗的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们有没有带吃的干粮,父亲一边笑一边把车辕交到我们的手里。
装了木头的架子车,像螺丝坏死了一样沉,拼足力气才能勉强挪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换下来的人并不闲着,大家拉的拉、推的推,车子一下子变轻了许多。
从山里拉回来的木头得用斧子劈成条状才能用来烧火。劈柴是个技术活,得像庖丁解牛一样,批大郤,道大窾,顺其自然。遇上纹理纠结的,往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劈开。没经验或者不小心,不是劈偏了砍到自己的脚,就是被飞起来的硬柴砸伤。当然,劈柴有劈柴的乐趣,特别是劈的顺手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快感,这大概就是劳动带给人的愉悦。
劈好的木材像一件漂亮的艺术品一样,摆放在门外的某个角落,遇上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硬柴才能派上用场。煮肉、熬汤、蒸馍、做豆腐、炒菜,样样需要强火,到时候,只要把风干的硬柴往炉膛里一添,火势当下就不一样了,原本平静的汤锅马上会变得沸腾。
(图片均来自网络)因为煤炭的使用和林木管理的强化,拉硬柴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但拉柴过程中的那些艰辛和拉回家后那份喜悦,却让我们一直铭记到现在。
请随小编走近作者
个人简介:
傅兴奎,1985年毕业于庆阳师专中文系,甘肃省作协会员、庆阳市作协副主席。20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先后在各类刊物上发表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出版《与清风对坐》《高考作文应试与写作》《作文知识能力点训练》《城乡纪事》等著作。
蝶舞轩生活馆
微信号:Angel520222
QQ330374252
诗歌|散文|摄影|绘画|随笔|杂谈
责任主编:乐 子
图文美编:Angel
QQ号:664185290 553131983
投稿信箱:66418529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