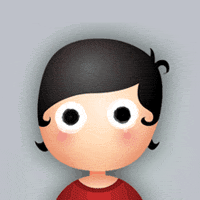破壳计划 ✖ 我为什么创作?
“破壳计划”由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BCAF)联合优质出版品牌“理想国”及多家学术支持机构共同发起,支持40周岁以下、没有纸质书出版经验的青年创作者出版第一本书。
8月15日上午“破壳计划”正式发布,下午13:47,我们就收到了第一封漫画组的申请邮件。然后陆陆续续,小说、诗歌、非虚构组都迎来了各自的第一封投稿邮件。申请者的年龄从生于1976到生于2005,所在地包括北京、上海、河北、河南、辽宁、吉林、甘肃、陕西、青海、安徽、江西、山东、江苏、浙江、广东、香港、纽约、伦敦。截至8月16日晚24:00,短短两天,已经有45位“有准备的人”向“破壳计划”发送了他们的书稿。
当然,速度不是最重要的。“破壳计划”有两个半月的申请期,我们也鼓励还没有准备好的创作者们再耐心打磨一下自己的作品,注意字数、格式等申请要求,详情请戳下方链接:
在申请表中,我们向所有创作者提问:你为什么创作?同样是这个问题,我们也问过“破壳计划”的12位终选评委。我们想知道,那个让你不得不做点什么、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内在驱动力到底是什么。下面是他们的回答。申请人的答案采用了匿名的方式,以及,出现或没有出现在这里,都不会影响评委对作品的判断。
“破壳计划”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两个半月,我们期待着收到更多让我们惊讶和迫不及待想要点开读一读的作品。
破壳计划
12位终选评委 ✖ 我为什么创作
小说组
按姓氏首字母A-Z排列
金宇澄,作家、《上海文学》执行主编
我眼前一直是有读者的,把我知道的事告诉他们,是写作的基本动力——等于年轻时给朋友写信,一直面对着对方,从不会孤独。我非常认同博尔赫斯的主张——他认为文学要义就是:“给读者消遣与感动,不醒世劝化”。
余华,作家
二十年多前,我是一名牙科医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手握钢钳,每天拨牙长达八个小时。我所在的医院以拨牙为主,只有二十来人,因牙疼难忍前来治病的人都把我们的医院叫成“牙齿店”,很少有人认为我们是一家医院。与牙科医生这个现在已经知识分子化的职业相比,我觉得自己其实是一名店员。
我就是那时候开始写作的。我在“牙齿店”干了五年,观看了数以万计的张开的嘴巴,我感到无聊之极,我倒是知道了世界上什么地方最没有风景,就是在嘴巴里。当时,我经常站在临街的窗前,看到在文化馆工作的人整日在大街上游手好闲地走来走去,心里十分羡慕。有一次我问一位在文化馆工作的人,问他为什么经常在大街上游玩?他告诉我:这就是他的工作。我心想这样的工作我也喜欢。于是我决定写作,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入文化馆。当时进入文化馆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学会作曲;二是学会绘画;三就是写作。对我来说,作曲和绘画太难了,而写作只要认识汉字就行,我只能写作了。
张旭东,学者、批评家
“批评即创作”本是老生常谈,但对于我却是一个不断更新的问题和挑战。回答“这个故事说了什么”带来的不是“用更无趣的语言把这个故事重讲一遍”,而是形形色色其他相关的故事。如果我们不但在“人物”、“情节”和“动作”的意义上,而且还在语言、观念、历史经验的意义上理解“相关的故事”,那么批评正是文学的完成,而具体文学作品、文学运动、文学风格本身,则永远处在“未完成状态”。批评对文学创作的“依附性”只是表面现象,因为它们是同一社会生产过程中两道相邻、却需要截然不同工序和技能的环节。同样,批评对文学的“评判”功能也是假象,因为批评其实不能也不可能比作品说出更多的东西:它只是把同样的东西再说一遍。只有被一再地、反复以不同方式说出来的东西,才构成我们的自我形象和自我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创作”都是解释,都是模仿,都是“评论”,反之亦然。它们都是人类经验和情感在黑暗中的彼此呼唤。
诗歌组
按姓氏首字母A-Z排列
胡续冬,诗人、译者、随笔作家
我年少时不安分,混社会、好勇斗狠,也喜欢学习,成绩始终很好。但无论是混帮派还是当学霸,都不能给我带来一种难以遏制的创造性快感。这种快感我读大学的时候在诗歌写作中找到了,后来随着写作的持续深入,我感到写作所带来的已经不止是那种难以名状的盛大快感,更多的是一种通过语言实现的与世界的隐秘对话。这种对话可能没什么特别激动人心的地方,但它足以让我神清气爽,足以让我愉快地继续写下去。
欧阳江河,诗人,诗学、音乐及文化批评家,《今天》文学社社长
我最初的创作起源于我喜欢诗歌,读了很多古诗、翻译诗,受到它们的感召和引领,没有更复杂的原因。但是越到后面,我写作的原因越复杂:自我想要得以汇集、得以表达,我对现实的感受,还有很多思想上的、历史上的、风格上的原因,汇聚成了我内在的创作原因以及推动力。
翟永明,诗人
我创作是因为从小喜欢诗歌,就想自己试一试写作。我开始写作之后,就想要创作出一种独特的自己的写作风格。当我的写作建立了一种风格之后,我就想要尝试多种不同风格的可能性。我对写作的探寻构成了我创作的原因和乐此不疲的热情。
非虚构组
按姓氏首字母A-Z排列
李娟,作家
我从小喜欢阅读和写作,不到十岁就有长大后成为作家的渴望,因为时间太过久远,已经说不清最初的动机是什么。只记得这个想法极其坚定,并为之付出长年累月的热情和努力。但坦率地说,是有功利心的。想依靠写作改变人生。因此,对时下四处滥用的“不忘初心”四个字非常不以为然。至少我自己的初心远不如此刻心来得纯粹靠谱。这也是自己这几十年写作的最大收获吧。
梁鸿,学者、作家
好像从记事起,文学就是我唯一的爱好。我沉迷于用语言创造情感和塑造氛围的那种感觉,人物慢慢浮现,世界依次展开,一切都在我的笔下生长,真是美妙不可言说。在少年时代,有一天傍晚走在乡村的路上,被大地的静谧和丰富所感动,以为一个人活着如果不描写春天、树木和大地,就不曾活着。现在想来,虽然极端,却仍然是最美妙的事情。
谢丁,新媒体非虚构平台《正午》主编
我认识一些朋友,似乎从小就有志于写作,他们在年少时就写了很多东西,练笔练了好多年。我不是,我很少有这种强烈的写作自觉性。在整个中学大学时代,我写得很少,但我喜欢写信,我们那时还用笔在信纸上写。写信让我更自由,因为有一个既定的读者,而且是朋友,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对我来说,写信最大的好处是,你从没有想着去迎合谁,也不用在乎别人的看法。
我始终相信,这种(写作的)自由比什么都重要。我写作的初衷也是这样,为了告诉朋友一则故事,一个想法,一段经历。写作其实是分享,慢慢地,陌生的读者也成了朋友。
漫画组
按姓氏首字母A-Z排列
陆扬,艺术家
创作是我打发剩余生命的途径,光活着等死会很无聊的,所以就创作创作让时间过得快一点吧。
温凌,艺术家
我想复制和传播自己的DNA。生儿育女可以实现这个愿望,我觉得创作作品也可以实现这个愿望。
烟囱,艺术家
有一些东西要表达,觉得非要自己做不可,所以必须自己动手了。
破壳计划
部分申请者 ✖ 我为什么创作
一直以来,我将写作看作是我最接近神灵的一种方式。当然,我也可以这么回答,比如说写作是我与时代对话的一种手段,写作是我肉身对灵魂的呐喊,写作让我再次回到了遥远的故土,让我以一种审视的眼光去打量故土的一草一木,但这些,都不是我目前最深刻的体会。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渐渐将写作当成了做梦,梦里,我可以奔跑,可以从十层楼上一跃而下,可以倒立在人间,可以不费气力就能将大山从愚公门前移开,这种状态下,我似乎是脱离了人世烟云,好像走进了另外一个黑暗而又深邃的世界,面对星辰,我独自前行,虽孤寂,却甚感快乐,每回就在我快要放弃的关头,前方的坡头上突然闪动了一下火光,我又以比之前更加饱满的劲头迎了上去,这种方式,是必然处于夜晚的,是必然远离热闹的空气的,是一种个人暗暗观望的偷窥,日光一晒,它就萎缩,直至隐身。我将它称之为梦。
我想或许最主要是因为好奇和对其他可能的渴望。曾经读兰波诗曰“我要成为所有人”,虽然最终发现我不可能成为兰波,那样的肆然生活,真的如其所说过完短暂但精彩的一生,但通过写作,讲述那些或幻想或曾见过听过的他人的生活,也同时在丰富着自己唯一生活里的其他可能。有太多可能存在,并且很多是同时存在,就像弗罗斯特诗里说的那两条“林间小路”,我们最终只能选择一条,但生活却似乎远远不仅仅如此。
与此同时,也发现对于问题庞大,而时常没有回答的恐慌同样是写作动力。有太多未知,虽然写作不可能真的对其作出准确的回答,但却是一种尝试,就好似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在荒诞里创造意义。
创作是一种“无中生有”的过程,就像一个生命的诞生。生命的存在加上意识的创作,共同形成了作为创作者的我,换言之,只有两者叠加,我才是我。
我认为每一篇故事都是某段生活的横截面,有些或许还闪耀着当初的光芒,或流淌着过往的热泪,原来故事本身即是回忆。小说暂代了大脑,替我储存某些我彼时想要淡忘,但将来势必会想起的回忆。我理想中的小说就是一个记忆收集器。每当我正在进行中的生活百无聊赖时,我就会拉开记忆收集器的某个抽屉。这些抽屉有的盛放着欢乐时光,有的装着凄风苦雨,有的则是毫无意义的晃悠。
看到这些抽屉,我的大脑就会沸腾不已,多么神奇,已经过去很久的事物竟然还能如此鲜活。我觉得这就是我写作的最大意义:让回忆与当下并肩。我的人生是复眼,能同时窥测到过去的,现在的,倘若我想,我甚至还能看到未来。
我是因为快乐才写小说,但现实是,我考不上本科专科,因为英语课写小说而只能读高职,以后做一些工资不高的工作,我疯狂读书,试图和别人跑在同一水平线,从史哲到政法,从独自一人的阅览室到怂恿舍友一起读高华,从爸爸对我怒吼“你写那些东西有什么用,有多少作家画家都饿死”到他别过脸去说“你写那些东西别熬夜,熬坏身体做什么也白费”,写小说,贯穿了我7年光阴和人事,每次拿一张白纸画剧情图,我就很快乐,忘记大伯叫我学汽修时的眼神,忘记高职老师收掉我不听课而自学汉语文学教材的事情。二十一岁的我坚信,无论我能不能出版著作,能不能拿到稿费,没关系,回到原点,没有任何比赛和酬劳,因为写小说才快乐。
我写,故我在。
我只会干这个,不会干别的,而且在其中可以得到快乐和解脱。此外,也妄想着我的写作可以为当代汉语文学增添一点点东西,比如心灵之苦楚和语言的韵律。
如果说讲故事就像在喂养心里的一头鲸鱼,我知道它巨大的躯体一直处于空洞的状态,我能做的就是不断地喂食,我不能让它饿死,那样的话,鲸鱼巨大的身体就会慢慢腐烂,慢慢发出恶臭,我在心里养着这头鲸鱼,不希望自己跟着腐烂跟着发出恶臭。
用文字创造一个幻境,有时感觉活在自己的幻境里比活在现实里自由一点,欲生便生,欲死便死。其实不太喜欢写作,有时候感觉写小说像是在。但是又停不下笔,想着这一篇写完就再也不写,这是最后一篇写完就好,但是写完之后,心里一出现意象又会奋不顾身地去写。就像一个一直准备的人,为了更好的,就将眼前的每一天活好,以此活了很久,一直准备一直都没有。如此而已。
不会其它手艺。
以前在荒无人烟的山里工作,自由支配时间很多,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只有写东西来打发时间,后来逐渐形成习惯。
我尤其崇敬那些不动声色但是饱含深意的谈吐。出于模仿欲望和自我挑战,我开始创作。如果有一天我能如我所愿地接近那些聪明人的境界,在艰难的世道里我应该能体会到极大的尊严。
我喜欢漫画,想用这个创作工具来解决一些困惑。
放空,不去想太多,只是画出心中所想和看到的样子。
点击查看
发现文化创新,推动艺术公益
微信公众号:bjbcaf
新浪微博:@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