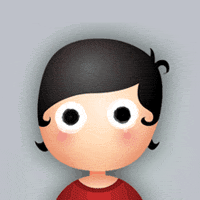付林鹏丨丨行人制度与先秦“采诗说”新论
行人制度与先秦“采诗说”新论
付林鹏
【内容提要】对于《诗经》的结集,有“行人采诗”的说法。但以往之研究,对此说多有怀疑。但通过对先秦行人制度的考察,会发现在众多王官中,确实只有行人之官具备采诗的可能性:首先,在众多王官中,只有行人系统能将不同方言区的歌谣转译为雅言;其次,在行人出使各国时,有考察各国风俗的职责,而歌谣恰恰是各地风俗的最好反映;最后,行人的聘使四方,也使他们具备接触各地民谣的可能性。故从很大程度上说,《国风》的编订,行人之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关键词】行人;采诗;《国风》
对《诗经》的结集,汉代有“行人采诗”之说,如刘歆《与扬雄书》言:“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逌(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班固《汉书·艺文志》亦云:“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又《食货志》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言行人之官即采诗之官。可见,此为汉人成说,殆无疑义。但后人对此多有怀疑者,或以为先秦之书不见采诗之说,或以为这是据汉乐府采诗之事所作臆测之辞,或以为这是故意为封建统治者吹嘘之辞,众说纷纭。[ 如崔述、夏承焘、高亨等人都有怀疑。可参见洪湛侯《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页。]但后人否定之辞,也多为臆断,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故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对先秦的行人制度追源溯流,才能辨析疑义,有所发明。
一、纳言、遒人制与上古行人制度的萌芽
行人制度,起源甚早。但在各代名称却有不同,于舜时有“纳言”,于夏时有“遒人”,于周时则有大、小行人之官。其名虽异,职守却大致相同,不外乎掌出使、通聘问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连带职能。但因时代不同,其职守有繁简之别。下面即从历时性角度,对先秦行人制度的形成机制及职能演进做一简要追溯。
相传虞舜时开始设官分职,立“纳言”一职。在《尚书》中,“纳言”有两义,一作名词解,是职官之名,即《尧典》所载帝舜之言:“龙!……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一作动词解,是一种进言方式,即《皋陶谟》所载:“工以纳言。”而其前一义恐怕是由后一义引申而来。因为在甲骨文中,“入”、“内”、“纳”三字同源,《史记·五帝本纪》就将“出纳朕命”改为“出入朕命”。故“纳言”即“入言”,原是一种由下达上的单向沟通方式。但其成为职官后,负责“出纳朕命”,成为上下间双向沟通的重要媒介。故孔安国传:“纳言,喉舌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尧、舜时期,尚处于酋邦时代,、夏联合的部落联盟。《尚书》中即屡称“协和万邦”、“万邦咸宁”,可见当时万邦林立,分散各地。而各部落间的沟通渠道并不发达,氏族议事会的决定需要下达,各部落间的意见也需要上传,故纳言一职应运而生。
关于“纳言”的沟通方式,据《皋陶谟》载帝舜言:“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汝听。”此句因错讹关系,颇为费解:一在于“在治忽”句意不明。据《汉书·律历志》“在治忽”当为“七始咏”之误。[ 据《汉书·律历志》所引,原文当做“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七始咏,以出内五言,女听”。顾颉刚、刘起釪对此有详细考辩,可参见《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50—451页。]郑玄《尚书大传》注:“七始,黄钟、林钟、大簇、南吕、姑洗、应钟、蕤宾也。”与五声、八音均指乐律而言;二在于“五言”涵义不清。对此,历代学者有不同说解。[ 有释为五常之言者,如《伪孔传》、《汉书·律历志》等主之;有释为诗者,宋人多主此论,如苏轼、叶梦得、蔡沈等都主此说;有释为五方之言者,如近人曾运乾等主之。可参见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51—452页。]大致而言,曾云乾将其释为“五方声诗”,是明智之举。因《礼记·王制》言:“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道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四方之外,再合之中国,便为五方。此虽为汉人之说,却也于理可通,如《吕氏春秋·音初》就载有四方之音的起源。当然,文献记载并不代表历史真实。但可以肯定的是,尧、舜之时,万邦林立,不同部落间的语言肯定也不相同。那么作为既要传达高层决策,又要替部落成员建言的“纳言”及其属官,肯定有转译这些部落间语言的职责。正如《周礼》载大行人的职责有“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象胥类似后代的翻译,其所学“言语”尚从大行人那里而来,作为与行人之官相类的“纳言”肯定也是通各方“言语”的。故纳言之职责,就是采集各方民情,将五方之歌诗进行转译,然后协之于“六律、五声、八音、七始”,以备帝舜及其大臣们审听。这恐怕就是“采诗”制的最早雏形。
正因如此,“纳言”的任官资格非常特殊,必须由精通乐舞的部落首领兼任。如最早担任“纳言”一职的是“龙”,与乐官关系密切。《尧典》将夔、龙并提,其中夔为典乐,证明其技术职能有相似之处。《大戴礼记·五帝德》也载尧时“伯夷主礼,龙、夔教舞”,注云:“龙、夔,二臣名。舞,谓乐舞。”在上古的神话传说中,也有“龙”典司乐舞的记载,如《山海经·海内经》载帝俊时晏龙制造过琴瑟,《吕氏春秋·古乐》载颛顼时命飞龙“作效八风之音”而创作了《承云》。古代氏族名号相承,职责亦相传,因此,“龙”很可能就是一个世代相传并精通乐舞的部族首领的称号。而《皋陶谟》也云:“工以纳言。”据孔疏解释:“《礼》通谓乐官为工,知工是乐官。”这些“工”很可能就是纳言的属官。
作为舜设九官之一,[ 《尚书·尧典》载舜时的部落联盟中,有十二牧、四岳、九官共二十二人的职官体系。其中九官是:伯禹为司空,弃为后稷,契为司徒,皋陶为士,垂为共工,益为虞,伯夷为秩宗,夔为典乐,龙为纳言。]“纳言”职责甚重,一些具体的工作,恐怕还是由其属官完成。有人就将“纳言”比拟为后代的“尚书”,《北堂书钞·设官部》引郑玄注:“纳言,如今尚书,管主喉舌也。”蔡沈《书集传》也认为“纳言”有“命令政教,必使审之”的职责,“周之内史,汉之尚书,魏晋以来所谓中书、门下者,皆此职也”。其实此说并不精确,如《史记·五帝本纪》亦载:“龙主宾客,远人至。”与《周礼·秋官》中大、小行人的掌宾客之礼的职责很相似,亦证明其为行人类职官。因为虞舜时代处于原始社会晚期,即便已有职官的设立,也相当简略,不似后代那样体系完备,职责分明。也许周代的大、小行人和内史都脱胎于虞舜时的“纳言”一职,也未可知。
夏代则有遒人,如《左传·襄公十四年》引《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也属行人之官。“徇”字在古汉语中义项颇多,其中既有宣示之义,又有谋求之义。故据注疏者解释,遒人之职能有二:其一,宣令之官。《尚书·胤征》孔安国注:“遒人,为宣令之官。木铎,金铃木舌,所以振文教也。”其二,采诗之官。杜预注:“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歌谣之言。”遒人在宣令和采诗时使用的乐器是木铎,许慎《说文》云:“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而木铎为“金铃木舌”,据古文字学者研究,“纳言”的“言”字在甲骨文中与“(告)”、“
(舌)”为一字之异构,“
”象木铎倒置之形,其上之“
”与“
”、“
”均为铎舌。[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页。]这说明“纳言”之职的建立也可能与乐器“木铎”有关。考古学证明了木铎起源很早,木铎之前身为陶铃,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仰韶、大汶口、龙山等文化遗址中就有陶铃出土,现存最早的铜铃则见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3296号墓中,墓地时代属于陶寺文化晚期,正好在夏代建国前后。[ 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页。]这既说明《夏书》关于遒人制的存在较为可信,也说明其存在的渊源很早。
遒人与纳言在职位十分相似,但在地位上则有很大区别。纳言地位很高,是部落联盟首领身边的重要决策者之一,不可能亲自去宣令和采诗;遒人可能与其属官相似,是宣令、采诗工作的具体实施者。故可以大致推测,遒人一方面负责将上层的决策传达下去,另一方面将下层的意见以歌谣的形式采集上来,然后交由其长官做具体的处理。或转译,或配乐,然后再献给统治者做决策参考。
至于商代是否有行人之官,文献不载。然由《礼记·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可知殷代官制已大为丰富,当也由行人类职官的存在。在甲骨卜辞中,有以“言”为名的职官,如罗振玉《殷墟书契后编》下23.1载:“王其从言各兕。”或与纳言之职有关。[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页。]
二、周代的行人机构与培养机制
周代有大、小行人之职,《周礼·秋官·叙官》载其属官有:“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仪,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此外,环人、象胥、掌客、掌讶、掌交等与交通诸侯有关者,恐怕也归大行人节制。据不完全统计,包括服役的府、史、胥、徒在内,周之行人系统内有524人之多。[ 其中,《周礼·秋官·叙官》载象胥属官为:“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翟”,同“狄”,为蛮夷闽貉戎狄六族之总称,故共有181人;而“掌客”之徒有“二十人”和“三十人”两说,现据阮元校,定为二十人。郑玄、贾公彦《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72页。]由此可知,周之行人系统已十分发达,并有着明确的层级区分和职能分工。
周行人之职,有常设与兼官之别:常设者如前之大、小行人及其属官,见诸史籍者,像《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载晋“栾盈过于周,周西鄙掠之,辞于行人”,杜预注为“王行人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载:“卫君入朝于周,周行人问其号。”都是周王室的行人。各诸侯国亦设有行人之官,如晋国有行人子员、行人子朱,郑国有公孙黑世代为行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郑伯有使公孙黑如楚,辞曰:‘楚、郑方恶,而使余往,是杀余也。’伯有曰:‘世行也。’”世行,杜预注为:“世为行人。”《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09页。]兼官则“其在本国皆另有本职,行人乃其临时兼职”,[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34页。]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统计:“行人见于《经》者六,并以见执书,是乃一时奉使,非专官。”[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75页。]这些人都是因被执而书,尚属偶然,相信春秋时期兼职行人并不在少数。当时担任兼职行人者,上至公卿,下至士人,或因人而设官,或临危而受命,不一而足。但不可否认的是,行人之官的普遍素质都比较高,其身份也多属宗法贵族的上层,受过良好的国子教育。故能于出使专对间、言辞揖让间,消弭危机,完成使命。
从爵秩上看,周之大行人为中大夫,小行人为下大夫。比之于诸侯国,则由上大夫、中大夫担任,《左传·成公三年》即言:“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这一记述,可明两事:一为《周礼》的爵位设置并非向壁虚造;二是周之大小行人的爵称可比之大诸侯的上大夫、中大夫。郑国公孙黑世为行人,其爵即为上大夫,[《左传·昭公元年》载子产言曰:“子皙,上大夫。”(《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22页)子皙即公孙黑之字。]相当与周之大行人。
周行人的培养,出自西周的国子教育。从身份维度看,国子即“国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当学者”,[ 《周礼·春官·大司乐》郑玄注,《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87页。]《礼记·王制》则以“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均为国子,涵括了内爵体系的所有子弟,自然也包括爵秩为中、下大夫的行人子弟。
从培养体制看,国子所受教育范围颇广。师氏以“三德”、“三行”教国子,负责国子的道德培养和行为规范;保氏以“六艺”、“六仪”教国子,负责国子的能力培养和礼仪规范。[《周礼·地官》:“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30、731页。]但国子的知识结构更多来自乐官系统的培养,《周礼·春官》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治国之学政,负责以乐德、乐语、乐舞教国子;乐师以小舞、乐仪教国子;籥师掌教国子舞羽吹籥等;《礼记·王制》亦载乐正以《诗》《书》《礼》《乐》造士。这恰恰验证了俞正燮“通检三代以上书,乐之外无所谓学”的论断。[ 俞正燮《癸巳存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盖乐德在于涵养国子之道德品质,乐语在完善国子的沟通技巧,即便乐舞也能在贵族的交际中起到重要作用。[《左传·襄公十六年》:“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63页。]此皆礼乐文明教化下行人所应具备的基本操守和处世经验。
从选拔程序看,由国子升为行人必须经过一定的选拔和考量。《礼记·王制》载周代的任官程序为:
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凡入学以齿。将出学,小胥、大胥、小乐正简不帅教者以告于大乐正,大乐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学。不变,王亲视学。不变,王三日不举,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大致而言,这一选拔程序大致包括:
1.在进行国子教育时,由各乡层层选拔的造士与国君之嫡子、庶子及卿大夫的嫡子处于同一层面,按齿排序,共同接受乐正的教育。这时他们都是士爵,是职官系统的预备队。
2.将要毕业时,先淘汰那些不合格者。即由小胥、大胥及小乐正先挑选出那些“不帅教”者名单,报告给国君,国君会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等或亲自对其感化,若怙恶不悛,则流之四方。
3.优秀的毕业生由大乐正举荐给司马成为进士,再经过司马的辨论官材,才具备任官资格,享受爵位和俸禄。
这虽是周代选官的一般程序,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小行人的选拔也是遵循这一程序的。既然专职行人经过基础的国子教育,则司马在辨论官材时,肯定是因某方面才能特别突出才被委以此职的。齐桓公称霸,广求人才,管仲曾推荐隰朋,言曰:“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辨辞之刚柔,臣不如隰朋,请立为大行。”[ 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47页。]正因为管仲觉得在习礼和言语两方面不如隰朋,才荐其为大行人。
三、行人采诗的可能性
通过对行人培养和选拔机制的考察,可以看出,行人受过良好的国子教育,精通礼乐和辞令,为其采诗提供了必要的知识条件。但遗憾的是,在大、小行人的行政职责中,却并未发现其能采诗的直接证据。而且,从爵位上看,他们亦不会亲自到民间采诗。那么,“采诗制”是否真的存在过?如果存在其细节为何?又是由哪些人负责呢?如果将行人视为一个整体系统,不仅局限于大、小行人两个职官上,这些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因为,从行人系统的知识结构和行政执掌看,其确实具备采诗的资格。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代语转译与“采诗”的技术性处理。
现存《诗经》,存十五《国风》,涉及范围包括今之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等地。虽都属中原区域,但其方言、风俗、音调,在今日尚且不同,更遑论两周之时。春秋时,“州异国殊,情习不同”,[ 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册,第1175页。]这一状况是确实存在的。而夷、狄之国亦交错纵横,杂糅其间,语言、习俗更为迥异。《左传·襄公十四年》载戎子驹支对范宣子言:“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而在西周职官系统中,惟有行人系统能够起到沟通各地域的作用。如行人属官有象胥,又叫舌人,见于《国语·周语中》,据韦昭注:“能达异方之志,象胥之官”,即负责对少数民族语言的转译和传达。《周礼·春官》也载“象胥”的职责为“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行人出使中原各国,情况会好一些,可以用通行的雅言交流,但出于考察民俗的需要,相信也会携带精通各地方言的属官。
归结于《诗》,在搜集整理之前,现存《国风》中的很多诗歌,也肯定是由方言吟唱的。 至于“风”之含义,有释为歌谣者,若郑樵《诗辨妄》言:“风者出于风土,大概小夫夫贱隶妇人女子之言,其意虽远,而其言浅近重复,故谓之‘风’。”朱熹《诗集传》释“国风”亦云:“国者,诸侯所封之域,而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主要针对其歌辞而言。有释为曲调者,以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一文为代表[ 顾颉刚主编《古史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册,第645—646页。],其根据一为《大雅·嵩高篇》中“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二为《左传·成公九年》“钟仪乐操南音”,被范文子赞为“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其实,不管作何解,两说都强调了“风”的地域性特征。而据新出材料,“风”之义是声辞合一的,如上博简《孔子诗论》第3简谓《邦风》“其言文,其声善”,兼二者言之。故“采风”之义,不仅是采声调,亦采歌辞。行人既受国子之教,精通乐语,故能“采声”;又因出使需要,精通各地方言,故能“采诗”。
另外,行人还负责对方言歌辞进行转译。前引刘歆《与扬雄书》载行人有“求代语”之责。代语,据郭璞《方言》注:“凡以异语相易谓之代也。”即各方言之间的转译词。《方言》全名《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就是扬雄搜集先秦至两汉间各地代语的著作,其体例则“悈鳃、乾都、耇、革,老也。皆南楚江湘之间代语也”之类。从情理而言,这一制度是存在的。古代典籍中亦有此类实例,如《说苑》卷十一所载之《越人歌》,原为“越语”:
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踰渗惿随河湖。
后经鄂君子皙随行之“越译”转译为“楚语”:
今夕何夕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鄂君子皙即楚共王之子黑肱,为春秋时人。《说苑》记事,虽有向壁虚造者,但多数春秋列国间故事还是有据可依的。《越人歌》的翻译,采用了意译和记音直译相结合的方式,是我国最早的文学翻译作品。[ 钱玉趾《中国最早的文学翻译作品<越人歌>》,《中国文化》第19、20期。]相信《国风》中的结集,也经过这样的转译过程,即由各诸侯国语言转译为雅言。[ 钱穆《读<诗经>》一文云:“今传《二南》二十五篇,或部分酌取南人之歌意,或部分全袭南人之歌句;然至少必经一番文字雅译工夫,然后乃能获得当时全国各地之普遍共喻,而后始具文学的价值。”《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139页。]《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正说明了是有方言诗的存在。即便在汉代,亦有大量方言诗的存在,《汉书·艺文志》载:
《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淮南歌诗》四篇。《左冯翊秦歌诗》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五篇。《河东蒲反歌诗》一篇。……《雒阳歌诗》四篇。《河南周歌诗》七篇。《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
亦与《国风》整理前之形态相似,其中有“歌诗”,是对歌辞之搜集;“声曲折”,则是对曲调之搜集。由此,亦可见“风”的声辞合一。
第二,博采风俗与“采诗”的功能性使用。
历代有关“采诗”之记载,细节虽有不同,但目的却是一致的,即博采风俗以观民风。[《史记·乐书》所载:“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亦是“采诗”之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册,第1175页。]如《汉书·艺文志》“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食货志》说“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宣公十五年》也说“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孔丛子·巡狩》则说天子“命史采民诗谣,以观其风”。另外,《礼记·王制》载太师陈诗之制也可“以观民风”,陈诗是采诗的下一步工作,故其目的是相同的。
近代研究者却多不信此说,或认为此举是出于对封建统治者的吹嘘,或认为是后儒增饰之词,并非采诗的真正动机。[ 洪湛侯《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页。]但据新出材料,这些说法是错误的,上博简《孔子诗论》第3简:“《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多数研究者认为,上博简抄录时间应不晚于战国中期,是可信的先秦文献,其思想可能出自孔子,撰写者则是其弟子。[ 可参见晁福林《从王权观念变化看上博简<诗论>的作者及时代》,《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廖名春《上博<诗论>简的作者和作年——兼论子羔也可能传<诗>》,《齐鲁学刊》2002年第2期。]这就大大提升了对采诗说的认识。其中,“溥观人俗”即普观民风民俗;“敛材”原指收集物资,引申为收集邦风佳作,即“采风”。[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130页。]而在《诗论》中,孔子评诗59篇,屡次提到“民性固然”的话。可见,正是通过对《邦风》的解读,了解其中所反映的民性,也即民俗。试举一例,如16简引孔子曰:“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诗,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反一本。”这说明,周代采诗以观民风的制度,并非汉人所臆造。
但遗憾的是,行人采诗之事,在《周礼》中却没有具体记载。不过,没有具体记载,并不代表没有留下线索。《周礼·秋官》在提到小行人出使各国时,有考察各国风俗的职责:
及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其悖逆、、作慝、犹犯令者为一书,其札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其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凡此五物者,每国辨异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贾公彦疏云:“此总陈小行人使适四方,所采风俗善恶之事。”这里有若干细节,可兹注意:其一,行人采风俗,以五物为标准,每国辨异之。即以“五事各自为总编,又以每国别异其子目也”,[ 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008页。]与《国风》按国别分类相似;其二,行人所采风俗,按五事各为一书,即扬雄《答刘歆书》所谓“尝闻先代輶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中的“奏籍之书”;其三,行人采风俗之目的,在于使天子“周知天下之故”,即班固所云“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由此可知,行人采诗只是“五物”的细目,所不载者,是因为已包含其中,毋庸赘言而已。后人不察,遂以为《周礼》不载“采诗”之事。这就解决了为何采诗的问题。
第三,聘使四方与“采诗”的可能性接触。
行人之官除负责接待各国宾客外,还有出使职责,如大行人:“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岁遍存;三岁遍覜;五岁遍省。”基本每年都会派使者前往各邦国慰问;小行人:“使适四方,协九仪。宾客之礼:朝、觐、宗、遇、会同,君之礼也;存、覜、省、聘、问,臣之礼也。”负责具体的出使事仪;行夫的职责则为“掌邦国传遽之小事,媺恶而无礼者。凡其使也,必以旌节,虽道有难而不时,必达”,据孙诒让解释,“周时传遽,盖用轻车,取其速至。故《方言》扬雄《答刘歆书》以行人为輶轩使者,輶轩即轻车也。行夫,亦即行人之属”,[ 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058页。]在出使他国时,行夫还“掌行人之劳辱事”,即为大、小行人干一些繁杂低贱之事。因此,不管从身份还是从职能上看,行夫最有可能是采诗的实际操作者。
行夫出使四方,大大增加了接触各国民谣的可能性。《国风》所收,有出自市闾者,有出自乡间者。出自市闾者,即朱熹所谓“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 朱熹《诗集传》,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若《卫风·硕人》是卫人有感于庄姜美而无子所赋,《郑风·将仲子》言男女欢爱之事,恐怕都出自巷闾,而且《国语·晋语六》载,古之王者听政,要“风听胪言于巿,辨祅祥于谣”,大概都是此类。出自乡间者,则班固所谓“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如《周南·芣苢》、《魏风·十亩之间》、《豳风·七月》等,非亲经农事者,恐不能道出。行人出使时,不能不涉市闾,出于对风俗的了解,自会接触到一些里巷歌谣。但其于乡间采诗,则稍多疑点。即便身为下士的行夫,也是贵族的一部分,是否能经常接触乡间的民谣?其实,这也是有可能的。,在五鹿还有乞食野人之事。另外,还可拿《陌上桑》里的“使君”为例,阎步克先生通过对汉代官制的详细考证,认为《陌上桑》里提到的使君,只不过是一名低级使者,因此,才有机会跟采桑女罗敷相遇。[ 阎步克《乐府诗<陌上桑>中的“使君”与“五马”》,《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此虽汉代故事,但却为先秦行人的采诗提供了一种启示,即行夫的身份与《陌上桑》中的“使君”有相似之处,从而为采集民谣提供了便利性。
《国风》之外,《左传》还载有很多民谣,句式多用四言,与《诗经》相似。如襄公十七年有“筑者讴曰”、昭公十二年有“乡人或歌之曰”、定公五年有“莱人歌之曰”等,均属市闾歌谣;定公十四年则有“野人歌之曰”属乡间民谣。这些歌谣被史官记录下来,也为行人采诗的可行性提供了旁证。可以说,这基本解决了由何人采诗的问题。
由此,本文可做出一种假设,即大、小行人在出使各邦国时,还有采风观俗的职能,其具体事宜是由手下的行夫去做。《周礼》设行夫三十二人,爵秩为下士,平时的职责是乘轻车前往诸侯国传达小事,只有在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时,才负责到乡野田间去采集歌谣;若随大、小行人留居于出使国,还负责采集里巷歌谣。然后再交由小行人,经过言语转译的处理,编为一书。回国后再由太师“比其音律”,以为天子观风之用。
四、《国风》采集的多种途径
可以肯定的是,《诗经》的结集途径并不单一,“采诗”仅是其中一方面。至于采诗之人,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据张西堂统计,有轩车使者、逌人使者、采诗之官、老而无子者、国史、孔子等说。[ 张西堂《诗经六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79页。]行人采诗之说,上文已论。但其他各说,相信也有某些依据的。
在这些说法中,形成了两派不同意见,即负责采诗之人来自周王室,还是诸侯国?第一派意见,认为由王官负责采诗,如前引班固之说,又《孔丛子·巡守》:“天子……命史采民诗谣,以观民风。”也赞成这一意见,但采诗之人却由行人变为史官。第二派意见,则认为由诸侯国派人采诗,曹魏时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宣公十五年》中云:
五谷毕入,民皆居宅,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家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以为由诸侯国各自采诗,且并无专官,由老而无子者临时兼任。那么,这两种意见孰是孰非呢?本文以为,两种情况应该同时存在。
从观风的角度,周天子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搜集诗歌:一是主动探求,二是被动接受。主动探求,即派出行人采诗,以了解各国风俗。现存十五《国风》中,肯定有一些是行人采集的。因为这十五国中,有国灭而名存者,若“邶、鄘灭于卫,桧灭于郑,魏灭于唐,皆附乎《卫》、《郑》、《唐》以见”,[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页。]而一些作于国灭之后的诗,仍被归于原来国家的名下。对此,朱熹颇感疑惑,他在《诗集传》中言:“邶、鄘地既入于卫,其诗皆为卫事,而犹系其故国之名,则不可晓。”但若从采诗和编诗角度,此事颇为易解,若是诸侯国所采,当然不存灭国之名;[ 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卫卿北宫文子引《邶风·柏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二句,但称为“卫诗”,由此可知卫人之态度。]若是王官所采,则按地域分类,也许会保留分封之初的国名。[ 顾炎武说:“邶、鄘、卫,本三监之地,自康叔之封未久而统于卫矣。采诗者犹存其旧名,谓之邶、鄘、卫。”顾炎武、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136页。]
被动接受,则是由诸侯国贡诗。清顾镇《虞东学诗》“迹熄《诗》亡说”条云:“盖王者之政,莫大于巡狩述职。巡狩则天子采风,述职则诸侯贡俗。太史陈之以考其得失,而庆让行焉,所谓迹也。”以为也分两个方面,即巡狩时诸侯所贡和述职时诸侯所贡。巡狩所贡,即大师陈诗,文有明载,如《礼记·王制》云天子有巡狩制度,其中有“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的环节。据孔颖达解释:
此谓王巡守见诸侯毕,乃命其方诸侯大师,是掌乐之官各陈其国风之诗,以观其政令之善恶。若政善,诗辞亦善。政恶,则诗辞亦恶。观其诗则知君政善恶。
。但恐怕是形式大于内容,相信没有几个国君会自曝其短,将“政恶”的一面展示给天子。据郑玄注,陈诗是“采其诗而视之”,则这些采诗人定出自诸侯国无疑,可能即何休所谓“老而无子”者,是半民间、半官方的下层“乐师”,也即民间艺人。[ 赵逵夫《诗的采集与<诗经>的成书》,《文史》2009年第2辑。]采诗时间在“十月尽正月止”,彼时“五谷毕入,民皆居宅”,是农闲季节。这与“行人”采诗的时间不同,班固以为行人于孟春之月采诗,刘歆《与扬雄书》则以为是“岁八月”,[ 其实,这并无矛盾,因《汉书·食货志》在叙述“采诗”前,有“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的记载,则言孟春时,民皆在野,岁八月时,民将入邑,都是与行人接触的最佳时机。故班言“孟春”,刘曰“八月”,都是笼统言之,其所指是一致的。]皆农忙之季。行人于农忙季节采诗,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触百姓,了解各国之疾苦;“老而无子”者则于农闲采诗,其方式是走家串户,可能与至今尚存在于甘肃、陕西、四川、宁夏一带的“春官”风俗相近。除采诗外,他们还有一重要职责,即宣传推广黄历。其活动时间则在腊月、正月之间,[ 赵逵夫先生对此做了有益的探讨,但其将先秦采诗诸说统一对待,未加以区别,则与本文意见不同。可参见《诗的采集与<诗经>的成书》,《文史》2009年第2辑。]正与何休所言的采诗时间相重叠。老而无子者将诗采回后,再经过一番“乡移于邑,邑移于国”的传播途径,最后由太师在典礼上陈给天子。而天子巡狩,必有史官随行,《礼记·礼运》言“王前巫而后史,卜巫瞽侑,皆在左右”,《汉书·艺文志》言“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巡狩如此重大之事,不能无史官随行。史官负责将各国诗谣进行记录整理,从而又形成了“国史采诗说”。[“国史采诗”之说,也是《诗经》成书的一大观点,如崔述在《读风偶识》中言:“旧说,周太史掌采列国之风,今自邶鄘以下十二国风,皆周太史巡行之所采也。”(崔述、顾颉刚《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43页)古人之所以有这种说法,恐怕就出于对天子巡狩采诗的误解。]
如果说巡狩是天子对诸侯国的主动考察,述职则是诸侯国对自己政绩的主动呈现。《左传·昭公五年》:“小有述职,大有巡功。”《孟子·梁惠王下》:“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述职之目的:一在于助祭,若《春秋公羊传解诂·桓公元年》云:“王者亦贵得天下之欢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之述其职。”是助祭时顺便述职;一在于纳贡,如司马相如《上林赋》:“夫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后汉纪·光武皇帝纪》:“诸侯朝聘,所以述职纳赋,尽其礼敬也。”期间是否有陈诗环节,史无明载,不敢妄言。
但《周礼·秋官》载“大行人”的职责中,有抚邦国诸侯之法,其中有“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传统注疏均以为,这是大行人把各诸侯国的象胥、瞽、史聚集到王宫进行培训。但本文以为,之所以将如此多的专业人才集中起来,也许有共同整理诗文本的意图在内。即在大行人的统筹带领下,由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文化官员共同协作,其中象胥负责言语的转译,史官负责文本的校理,[ 若《国语·鲁语下》谓“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可能就是文字校理工作。徐复观也指出:“诗与乐不可分,太师主乐,则诗当为太师所专主。但将歌唱之诗,书之简策,且将篇章加以编次,就当时的情形来说,则非史臣莫属。”徐复观《原史: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学的成立》,《两汉思想史》卷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乐官负责音律的谱写,毕竟本国之官对己国的方言、文字、土调更为熟悉。同时,这一过程,还是一个相互回馈的过程。一方面,各国乐官可能顺便将本国新采集到的诗歌,进献给周王朝,即所谓的“诸侯贡俗”;另一方面,周王室又将新整理好的《诗》教给瞽、史,以作为各国培养国子的教材。“谕书名”或包括对《诗》文本传授,“听声音”或是对新谱《诗》乐的学习。正因为如此,才有春秋时代赋诗的兴盛。
由此可见,《国风》的结集,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可能是很多文化官员共同协作的结果,而行人之官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最大。他们既采诗,又负责《诗》的整理;既将《诗》作为天子观风知政的首要途径,又将《诗》作为自己出使专对的重要手段。
《中国诗歌研究》 2013年00期
【第604期】
艮山杂志 微信号→ genshanshuyuan鼓励新知,免费开放, 欢迎订阅,欢迎投稿。 联系信箱:igensh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