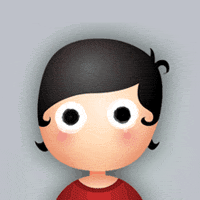【学术争鸣】三评张继龙《阿勒坦汗与土默特》:高级抄袭
三评张继龙《阿勒坦汗与土默特》:高级抄袭
晓 克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一
我的《再评张继龙﹤阿勒坦汗与土默特﹥》一文,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公众号“朔方论坛”面世后,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了反响。同时,也促使张继龙做出了“回应”。8月7日,他给我发来短信称:“看到你第二个东西了,这几天听众人的话没有行动,明天开始和你走程疗,……我有能为解释史籍中的每一句话,史籍的内容不是那个人的专利,我们到个评判公道的地方说吧,方面我更是有全新的观点,姓氏上有四十多个是我亲自收集整理,对云姓的解释也比于老师体会更深。”短短几句话,逻辑混乱,错别字不少,无法卒读,考虑到今后可能的法律责任,我只能原文照录。文中的“程疗”,大概是“程序”之误,“能为”应该是“能力”之误,而“那个人”,大约是要说“哪个人”。
在此,先就其短信所涉及的几个问题,简要说明一下。
首先是张继龙对待学术批评的态度。众所周知,在学术界开展学术批评是很正常的事情。在当前学术气氛浮躁,甚至学术腐败现象屡见不鲜的情况下,更是应该大力提倡开展学术批评。学术批评自有其规矩:批评、被批评的双方都应该仅限于通过发表批评、辩驳甚或是反批评文章,来摆事实,讲道理,以求明辨是非,促进学术研究不断发展。张继龙大约不太明白这样的规矩,或是不把这样的规矩当回事。我的前两篇评论文章公诸于世后,至今未见其撰写文章进行回应,等来的“回应”,却是再三给我发来短信,说什么:,我就以造谣诽谤告你了。不是有XX和XX的脸面我就直接找你了。”,看一看你发给人们发的东西,蠢猪一个。你这几天先到医院看一看红眼病和神经病吧。”如此不守规矩的“回应”实属罕见,不仅表明其学术素养之贫乏、处事方法之下作,更重要的是,他闯入学术界,抄袭他人论著,却容不得别人基于事实所作的批评,通过这样的“回应”,蔑视学术批评规则,威胁、谩骂他人,骄横暴戾之气,可见一斑。至于他说:“我们到个评判公道的地方说吧”,说明他认为学术界并不是一个“评判公道”的地方,不把相互开展学术批评当做评判公道的场合和途径。
其次是所谓的“史籍”问题。张继龙说:“我有能为解释史籍中的每一句话”。如上所述,“能为”应该是“能力”之误。我国的史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自古以来,众多文史学者“为解释史籍中的每一句话”而做了大量训诂、释义、考证、祛疑、疏证等工作,由此,形成了我国举世罕见的各门文史学问。许多前辈学者青灯黄卷,尽其一生,致力于这样的学问,皓首穷经。但并没有哪位先贤大言:“有能力解释史籍中的每一句话”。以张继龙的说法来看,这些先贤也太愚钝,这些学问更不必要,其对史籍和学问的理解竟然停留在如此业余的水平,真使人吃惊。张继龙又说:“史籍的内容不是那个人的专利”。“那”是“哪”的错别字。他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大约是:既然史籍不是哪个人的专利,那么大家就都可以利用。此话不错。然而,我前面两篇文章所批评的“抄袭”,是指他对别人论著的抄袭,而不是说他“抄袭”了某史籍。只要不是执意混淆是非,一般人都懂得,史籍记载本身与利用史籍记载研究后得出的创新性劳动成果(含:大到全篇小至段落的谋篇布局、个人化的叙述、章节目等的结构、文字叙述构思、独到的观点、全新的结论等等),完全不是同一概念,是泾渭分明、性质不同的两样东西。如果借口“史籍的内容不是哪个人的专利”,从而否定他人利用史籍记载研究后得出的创新性劳动成果的专属性,认为它也“不是哪个人的专利”,那么,世界上还有“抄袭”、“剽窃”可言吗?国家还有必要制定、实施《著作权法》吗?显然,张继龙的如此说法,难免使人产生驴唇不对马嘴、偷换概念的感觉,目的无非是要混水摸鱼,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窃取他人的劳动成果。
再者是对于前辈学者的态度。我的“再评”文章,指出了张继龙对乔吉先生《蒙古史 北元时期(1368~1634)》和于永发先生《志之余》二书的抄袭问题。对此,张继龙不是进行具体的说明或辩驳,反而大言:“方面我更是有全新的观点,姓氏上有四十多个是我亲自收集整理,对云姓的解释也比于老师体会更深”,试图以此来否认他对二位先生论著的抄袭。在内蒙古史研究及地方史研究学界,乔吉、于永发二位先生的学术造诣、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反观张继龙,遍查国内权威的期刊网“知网”以及“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没有见到此人发表过一篇文章,遑论作为学术研究必须的学术论文。这就使想通过阅读其论文的途径,了解其学术研究的基本领域以及所需具备的学术素养、研究能力、专业规范、知识积淀和研究基础等等,完全成为了不可能。就这样一个于2012年才开始涉足于土默特历史文化研究的人,在抄袭了上述二位先生的作品后,不仅无视他们的学术造诣和成果,对其缺乏起码的尊重,反而大言不惭地说:“方面(正确的说法应是“在史研究方面”)我更是有全新的观点”,“对云姓的解释也比于老师体会更深”,完全不把乔吉先生等学界众多从事史研究的专家放在眼中,不把于永发先生等地方史研究学者放在眼中!
这也难怪,对张继龙来说,这大概是一以贯之的。在张继龙的书中,没有一条注释,也就看不到一篇他曾经参考过的论文,书后只列了“主要参考书目”,当然,其中也见不到他参考过的论文的篇目。这就是说,张继龙在撰写他的书时,没有参考、借鉴、引用过一篇相关论文,在他眼中,前人的研究是一片空白,他的研究则是空前之作。不知是张继龙学术眼光太过“高傲”,对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毫不认可?还是他的学术视野太过狭窄,对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浑然不知?亦或是他的学术技巧太过“高明”,对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引用”后,再把痕迹抹掉,结果陷入了抄袭的境地?
二
言归正传,现在来说张继龙书中的“高级抄袭”现象。所谓“高级抄袭”,是指“经改头换面后将他人受著作权保护的独创成份窃为己有的行为”。可见,所谓“高级抄袭”是经过“改头换面”的抄袭,而窃为己有的是“他人受著作权保护的独创成份”,也就是上述“利用史籍记载研究后得出的创新性劳动成果”。要进行“改头换面”抄袭,就必须对原文作一些诸如改写、增删、拼接、位置调整等技术处理。有学者根据不同的处理技术,将其归纳为:搅拌式、组装式、拼凑式、掩耳盗铃式、偷意等形式。[6]
搅拌式抄袭。“将他人的话与自己的话搅拌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将他人论述的次序做些调整,便作为自己的话登场,是为‘搅拌式’。”来看张继龙在其《阿勒坦汗与土默特》(以下简称《阿勒坦汗》)一书中,是怎样操作的。《阿勒坦汗》第20页——21页:
1509年(明正德四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博罗特到河套地区,管理当时驻牧河套地区的蒙古永谢布、鄂尔多斯、蒙郭勒津部。但是,当乌鲁斯博罗特在祭奠成吉思汗的白室时,永谢布太师畏兀儿沁人亦卜剌(又译写为伊巴赉)和鄂尔多斯部领主满都赉阿哈勒呼率兵前来,寻衅杀死了乌鲁斯博罗特,挑起了对达延汗的叛乱。当时,巴尔斯博罗特正带着夫人博坦哈屯,长子衮必里克、次子阿勒坦寄居于驻牧河套的蒙郭勒津部领主火筛塔布囊(又译写为科賽)家中。火筛塔布囊的哈屯是满都鲁汗与满都海哈屯所生的也失格公主,也失格公主与巴尔斯博罗特为异父同母姐弟。据《蒙古源流》记载,事变发生后,火筛塔布囊和也失格公主商量说:“这孩子(巴尔斯博罗特)我们养不了了,还是送他回他父亲那里去吧。”随后,委托鄂尔多斯的帖木尔等六人、蒙郭勒津的必里克图将巴尔斯博罗特和他的夫人、长子衮必里克护送到达延汗处,而把3岁的阿勒坦寄养于蒙郭勒津人失你该·袄儿六、也别该阿噶家里。《阿勒坦汗传》记载的是把阿勒坦汗寄养于星凯乌尔鲁克(乌尔鲁克为职官名)、额伯凯乌由罕(乌由罕为官员妻子的尊称)的家中。不久,星凯乌尔鲁克、额伯凯乌由罕听到传闻,说亦卜剌太师欲加害幼小的阿勒坦,遂决定把他送回他祖父达延汗那里。额伯凯乌由罕与同部落的希尔玛鲁特乌尔鲁克和随从带着咿呀学语的阿勒坦昼伏夜行,阿勒坦平常时由拾柴的女仆悉心照料,行走时由扮作寡妇的人带在身边,,于1510年平安地见到了祖父达延汗。
《土默特史》第85页:
1509年(正德四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博罗特到右翼出任济农,意在控制右翼。但是,当乌鲁斯博罗特在祭奠成吉思汗的“白室”前叩拜时,畏兀特部人太师伊巴赉(亦卜剌太师)和鄂尔多斯部领主满都赉阿固勒呼率兵前来,寻衅击杀乌鲁斯博罗特济农,挑起了对达延汗的叛乱。当时,巴尔斯博罗特正带着夫人博同哈屯,长子衮必里克、次子阿勒坦等寄居于右翼蒙古蒙古勒津部首领科賽塔布囊(火筛)家中。科賽塔布囊的夫人是满都鲁汗与满都海夫人所生的伊锡克公主,伊锡克公主与巴尔斯博罗特为异父同母姐弟。据文献记载,当事变发生后,对于巴尔斯博罗特一家来说形势十分凶险,随时有被杀的可能。②伊锡克公主和科賽塔布囊商量道:“这孩子(巴尔斯博罗特)我们养不了了,还是送回他父亲那里去吧。”③随后,委托鄂尔多斯的帖木尔、蒙古勒津的必里图等七人将巴尔斯博罗特和他的夫人、长子护送到达延汗处,而把时年3岁的阿勒坦寄养于蒙古勒津人星凯乌尔鲁克、额伯凯乌由罕家中。不久,星凯乌尔鲁克、额伯凯乌由罕听到传闻,说伊巴赉太师欲加害幼小的阿勒坦,遂决定把他送回他祖父达延汗那里。额伯凯乌由罕亲自行动,由同部落的希尔玛鲁特乌尔鲁克陪同,带着阿勒坦“昼潜夜行伺机脱走”④,于1510年(正德五年)回到了达延汗身边。
对于《土默特史》的叙述,张继龙在抄袭时尽可能地作了“搅拌”:尽量更换了所涉及人物的译名,使之不同;对原文有所增删;在非关键部分改变一下说法等等,努力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淆效果。但读者不难发现,整段文字在叙事内容、语言风格、遣词造句方面的相似性,而在几个关键之处,除了人名译写或有所不同之外,可以说是一字不差。
既然是“搅拌”,就意味着对原文要进行改写。历史学研究的特点,是每句话都必须言之有据,不能信口雌黄。我的第二篇评论文章见诸“朔方论坛”公众号后,有网友留言:“历史人,宁坐十年冷板凳,不写一句空文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张继龙在改写别人的文字时是否有根据呢?
《土默特史》原文说:“当乌鲁斯博罗特在祭奠成吉思汗的‘白室’前叩拜时”,《阿勒坦汗》改写为:“当乌鲁斯博罗特在祭奠成吉思汗的白室时”,把原文中“前叩拜”三字随意删去,使在“白室”前叩拜,变成祭奠“白室”。“叩拜”与“祭奠”的意思不容混淆,这当无需多言。问题的关键是,在相关的蒙古文史籍中,都没有关于乌鲁斯博罗特“祭奠”成吉思汗白室的记载,只有《蒙古源流》明确记载为“叩拜”。张继龙改“叩拜”为“祭奠”,何据之有?如若不改,又需照抄,这确实使人进退维谷。
张继龙还将原文“寄居于右翼蒙古蒙古勒津部首领科賽塔布囊(火筛)家”,改为“寄居于驻牧河套的蒙郭勒津部领主火筛塔布囊(又译写为科賽)家中”。前人的记载和后人的研究都显示,此时,作为蒙古勒津部首领的科賽塔布囊早已驻牧于丰州滩(今土黙川)了。而张继龙这里的改动,也与其书第13至14页所作叙述自相矛盾:“分析《万历武功录》《蒙古黄金史纲》《蒙古源流》的记载可以确定,在1509年,在呼和浩特大黑河一带确实发生过达延汗与蒙郭勒津部的战争。……这时的呼和浩特地区仍由蒙郭勒津部驻牧”。可见,张继龙在“搅拌”过程中也未能认真下些功夫,把前后叙述协调一下,使之一致,结果就只能是顾此失彼,自相矛盾,前后冲突了。顺便说一句,即使是上述如此短的一句话,其中的语病也有不少。例如,所列三本书名之间,居然没有标点符号。真不能再细挑了,否则,难免使人感到有些“吹毛求疵”。
《阿勒坦汗》说,在阿勒坦被送回祖父达延汗处的途中,“。然而,遍查相关文献,,。这大概又是该书作者根据自己想象杜撰出来的吧。这样的杜撰,在文学创作中可谓神来之笔,在历史研究中却绝不容许。历史研究不同于文学创作,来不得半点虚构,必须言之有据,否则,就是对历史的玩弄,对读者的欺骗。
在文字方面,张继龙也是很不严谨。比如:《蒙古源流》记载,科賽与其妻商量说:“……还是送回他父亲那里去吧”;张继龙引作:“……还是送他回他父亲那里去吧”。在“送”和“回”二字间,凭空多了一个“他”字,使原本通顺的句子变成了病句。
组装式抄袭。“将别人书中不同场合说的话,组合在一起;一段话中,这几句剽自这一页,另几句袭自离得很远的一页,然后作为自己的话示人,是为‘组装式’”。对这样的手法,张继龙运用的同样得心应手。请看,《阿勒坦汗》第175页:
万历三年(1575年)十二月,明朝在甘肃镇边外的洪水扁都口为青海兵都等开市,规定每年互市一次,每次为期一月。初次开市,扁都口马市就交易官马二千一百零四匹,牛羊五十八双,商民交易马牛羊二万二千有余。开市后,青海蒙古各部也纷纷约束属下部属,让他们不得内犯骚扰明朝。
青海互市成功后,兵都台吉对来之不易的贸易机会十分珍惜,积极与明朝交易,甚至不顾明朝规定的定额,增加“贡马”的数量。万历六年(1578年),兵都台吉把“贡马”定额由八匹增为十匹。明朝经过协商,按十匹给予了赏赐,但声明今后不得额外加增。为了从互市上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兵都台吉改变了多进贡马匹的方法,转而设法向明朝谋求更多的互市市口。万历十二年(1584年),兵都、克臭向明朝提出了在洮河、河州开市,照各边讨赏的互市请求,但明朝没有批准。
这两个自然段,基本照抄了李文君《明代西海蒙古史研究》第204、205、206、207页中的几段话。这回采取的是跳跃组装式,即抄几句,便跳过若干字、若干句、若干行,接着再抄。为了节省篇幅,我在下面引文中张继龙跳跃得较完整的地方,用省略号表示,并在括弧里说明跳过多少行。李文君《明代西海蒙古史研究》:
万历三年(1575)十二月,明朝在甘肃镇边外的洪水扁都口为西海丙兔台吉等开市,规定每年互市一次,每次为期一月。……(此处跳过7行半)初次开市,扁都口、庄浪两市已“易官马二千一百零四匹,牛羊五十八双;商民易过马牛羊共二万二千有余”② 。……(此处跳过7行半)这之后,西海、松山各部又纷纷约束属下部众,让他们不得内犯骚扰明朝。……(此处跳过19行半)
西海互市成功后,西海丙兔台吉和松山宾兔台吉对来之不易的贸易机会很是珍惜,积极地与明朝做交易,甚至不顾明朝规定的定额,一再增加“贡马”的数量。万历六年(1578年),“丙兔台吉等九名贡马十匹,赏如例。先是,贡八匹永为定规,至是,加进二匹。部议:今次姑与给赏,以后不得过多,庶约誓一,而贡市可久。”④……(此处跳过5行)为了从市赏中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丙兔台吉等改变了多进贡马匹的策略,转而设法向明朝谋求更多的互市口岸。万历十二年(1584),“丙兔、克臭欲于洮州、河州开市,照各边讨赏”①……(此处跳过17字)明廷没有批准。
虽然有些跳跃,虽然在个别人物或部落名称、少数字句上有所变动,但这样的抄袭,还是一目了然的。
再来讨论一下抄袭中出现的错误或问题:
1、纪年问题。一般情况下,历史学研究者会在自己的论著中通篇使用相同的纪年方式,要么以公历纪年为主,括注农历纪年,如:“1575年(万历三年)”;要么以农历纪年为主,括注公历纪年,如:“万历三年(1575)”,这是最基本的学术素养。《土默特史》纪年如前者,《明代西海蒙古史研究》纪年如后者。在上揭《阿勒坦汗》的两段话中,前者抄自《土默特史》,保持了与《土默特史》相同的纪年方式;后者抄自《明代西海蒙古史研究》,纪年方式又完全与《明代西海蒙古史研究》一样。事情虽小,细微之处却更能说明张继龙学术素养之缺乏,同时,也使其抄袭行为露出了马脚。
2、地点问题。李文君原文:“初次开市,扁都口、庄浪两市已‘易官马二千一百零四匹,牛羊五十八双;商民易过马牛羊共二万二千有余’②”,引用文献记载说是在两处市口进行交易。而张继龙在抄袭过程中,将其改变为:“初次开市,扁都口马市就交易官马二千一百零四匹,牛羊五十八双,商民交易马牛羊二万二千有余”,不仅去掉引号,使之失去了出处,更甚者是将“扁都口”、“庄浪”两个市口中的“庄浪”随便删去,结果读者看到的是:这次交易只是在扁都口进行的,一处交易的牲畜就达到上述数量。如此严重歪曲历史事实,将历史当做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真是欺古人太甚,欺原作者太甚,欺读者太甚!更令人不齿的是,这样的妄改歪曲,在《阿勒坦汗》一书中随处可见,难以枚举。
3、主人公问题。张继龙在上引文中说:“开市后,青海蒙古各部也纷纷约束属下部属”,主人公是“青海蒙古各部”。李文君在原文中说:“这之后,西海、松山各部又纷纷约束属下部众”,主人公是“西海(即青海)、松山各部”。不难发现,张继龙又作弊了,他又随意把被其抄袭原文中的“松山”抹掉了。李文君所说“西海各部”,等同于张继龙所说“青海蒙古各部”,而李文君所说的“松山各部”,是指当时驻牧于“大、小松山”(今甘肃省天祝、永登、古浪、景泰等地区)的蒙古各部。难道说,张继龙竟然不知道“松山”与“西海”的区别,认为李文君行文重复才把“松山”抹掉?否则,作何解释?
4、语言问题。在改动被抄袭原文过程中,张继龙对遣词造句、文理通顺不以为然,经常把本来通顺流畅的原文,变得疙疙瘩瘩,难以卒读。比如,他说:“青海蒙古各部也纷纷约束属下部属”,这“属下部属”,读来就使人感到别扭,“属下”、“部属”连在一起,是同义重复。而在李文君的原文中的表述是:“西海、松山各部又纷纷约束属下部众”,“属下”修饰“部众”,行文是符合语法规范的,读起来也很顺畅。
拼凑式抄袭。将别人不同论著中说的话,各自取来,拼凑在一起,作为自己的话示人,是为“拼凑式”。看看张继龙在《阿勒坦汗》一书中是怎样拼凑的。《阿勒坦汗》第81页:
达延汗后裔征伐兀良哈的军事行动先后有六次,历时20多年,最早的四次是阿勒坦汗配合博迪汗以及阿勒坦汗之兄鄂尔多斯首领衮必里克进行的,后来的两次由阿勒坦汗单独完成。在《阿勒坦汗传》中,对这六次征伐兀良哈的情形有详细的记述,其中第一次征伐兀良哈的记述为:“……(此处略去所引记载)”
嘉靖三年(1524年),阿勒坦汗刚刚十八岁。这次参加征伐兀良哈,是所有史料中他参加战争的最早记载,。
《土默特史》第107页:
征伐兀良哈的军事行动先后六次,费时20多年,起先是阿勒坦汗配合小王子博迪汗以及阿勒坦汗之兄、鄂尔多斯万户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进行的,后来由阿勒坦汗独立完成彻底降服兀良哈的任务。在蒙文史书《阿勒坦汗传》中对这六次征伐兀良哈的情形有详细的描述。一征兀良哈:“……(此处略去所引记载)”
在以上《阿勒坦汗》、《土默特史》两段引文最后,出现了小小的差异:,《土默特史》却没有同样的内容。这个差异很让人生疑。《土默特史》这部分内容,是由薄音湖先生完成的。经过查阅同作者三十多年前的论文,找到了张继龙这段话的“出处”,它来自薄音湖《俺答汗征兀良哈史实》(《内蒙古大学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1982年10月)一文:
嘉靖三年(1524),俺答汗刚刚十八岁。这次参加征伐兀良哈,是所有史料中关于他活动的最早记载,。
原来,上揭张继龙的这段叙述,竟然是将薄音湖先生不同时间、不同论著中的两段文字拼凑在一起,一并窃为己有了。
为了掩人耳目,张继龙在费力拼凑之际也不忘妄改。《土默特史》原文中的“鄂尔多斯万户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被张继龙改为“鄂尔多斯首领衮必里克”。“鄂尔多斯”曾经是一个军事行政单位的名称,至今还是内蒙古一个地级市的名称。严格讲,名称本身并不是行政单位,所以“鄂尔多斯首领”是说不通的,是病句。薄音湖先生原文中的“是所有史料中关于他活动的最早记载”,被张继龙妄改为:“是所有史料中他参加战争的最早记载”。众所周知“活动”与“战争”的区别,“活动”泛指人的一切行为,具体到阿勒坦汗而言,所谓的“活动”,不仅指战争而言,、经济、宗教、文化、家庭及部落生活等各个方面,而“战争”仅仅就是战争。张继龙在没有列出文献依据,没有进行研究、考证的情况下,随意将“活动”改为“参加战争”,曲解了原文原意。
再看一例。张继龙《阿勒坦汗》第85页:
卫拉特部在13世纪以前,居住于色楞格河下游、叶尼塞河上游和贝加尔湖附近的广大森林地区,以斡亦剌、外剌、外剌台、斡亦剌惕等不同译名见于蒙元时期的史籍。关于斡亦剌惕人,拉施特主编的《史籍》记载说:“他们的外貌和语言与蒙古人类似。”据《元朝秘史》记载:“兔儿年,成吉思汗命拙赤率领右翼军出征森林部落,由不合担任向导。斡亦剌惕部的忽都合别乞先于土默斡亦剌惕部落前来投降,引导拙赤进入土默斡亦剌惕的失黑失惕地方。拙赤招降了斡亦剌惕、不里牙惕、秃巴思等部落,到达土默乞儿吉思部落。……”(此处略去16行半)当元帝国崩溃之后,他们乘黄金家族衰弱之机,崛起于西北。为了控制整个蒙古地区,他们对元宗室采取了斩尽杀绝的办法,乃至“杀元裔几尽”。从卫拉特首领猛哥贴木儿、马哈木,到脱欢、也先,经过百余年的激烈争战,卫拉特统一了东西两部蒙古。
曹永年:《关于卫喇特融化于蒙古的问题》(《卫拉特史论文集》,《新疆师范大学学报》专号,1987年):
卫喇特,十三世纪以前生活在以希什希德河为中心的叶尼塞河上游至色楞格河支流木伦河的广大森林地区,以斡亦剌、猥剌、外剌、外剌台、歪剌歹、外剌歹、斡亦剌惕等不同译名见于蒙元时期的史籍。
关于斡亦剌人,拉施特说:“他们的外貌和语言与蒙古人类似。”①用今天的标准看,属于蒙古语族。
《元朝秘史》云:“兔儿年,成吉思汗命拙赤领右手军去征林木中的百姓,令不合引路,斡亦剌种的忽都合别乞,比为万斡亦剌种先来归顺,就引拙赤去征斡亦剌。入至失黒失惕地面,斡亦剌诸种都投降了。”
薄音湖《俺答征卫拉特史实》(《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当元帝国崩溃之后,他们乘黄金家族衰弱之机崛起于西北。为了控制整个蒙古地区,……他们对元宗室采取斩尽杀绝的办法,乃至“杀元裔几尽”④。从卫拉特首领猛哥帖木儿、马哈木,到脱欢、也先,经过百余年的激烈争战,卫拉特统一了东西两部蒙古。
显然,这次张继龙是把曹永年先生的论述作为前半段,将薄音湖先生的论述作为后半段而拼凑在一起,一概不要什么冒号、引号、注释、“参见”等等,成为了他自己的一段论述。这“拼凑”手法,令人叹为观止。
这里还须指出,上揭《阿勒坦汗》文字中所引《元朝秘史》的记载,应该是出自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张继龙同样未对其注出版本),二者行文基本一致,但张继龙却把余大钧原文中的“秃绵”全部改为“土默”。尽管二者都是蒙古文“Tümen”(意为“万”)一词的音译,但在蒙古史学界却有约定俗成的不同用法,“秃绵”亦或写作“土绵”,一般用以指“万户”或“众”之义;“土默”却是鲜见的用例,只有在其后附加上表示复数的后缀成分“d”(汉文“特”),才可成为一个常见的名称“土默特”,是特定蒙古部落或旗的专称。
另外,在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原文中说道:“拙赤招降了斡亦剌惕、不里牙惕、巴儿浑、兀儿速惕、合卜合纳思、康合思、秃巴思等部落,到达土默乞儿吉思部落。”这里,余大钧先生把《四部丛刊》三编本《蒙古秘史》中相对应的内容全部、准确地译出了。在额尔登泰等《<蒙古秘史>校勘本》中,此处译作:“……入至失黑失惕地面,斡亦剌秃巴思诸种都投降了。至万乞儿吉思种处。”张继龙既然选择了余大钧先生的译本,却又不知何故将其中的巴儿浑、兀儿速惕、合卜合纳思、康合思这几个部落名删掉。看来,张继龙在利用文献记载方面也是十分随意的。
前面已经就张继龙的“搅拌式”、“组装式”、“拼凑式”抄袭作了评论,接下来该对“掩耳盗铃式”做些评论。但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先看此类抄袭的特点,“将别人的话原原本本地抄下来,或者抄录时稍做文字上的调整,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做一个注释,让读者‘参见’某某书,是为‘掩耳盗铃式’。”前文已经说过,在张继龙《阿勒坦汗》一书中,使人大跌眼镜、完全不守学术规范的是竟然没有一个注释,什么页下注、章后注、文末注等一概全无,甚至连文内注都没有。所以,他的“高级抄袭”手段尚未练就十八般武艺,缺少了“掩耳盗铃式”这一重要类型,取而代之的是我在《再评》一文中揭示的“明目张胆”、“奋不顾身”式的“低级抄袭”。
最后来看偷意。窃取他人的论述、观点、结论为己有,而在字句上尽量不留痕迹,是为“偷意”,“偷意”还可涵盖复制他人论著的谋篇布局、层次结构等。在这方面,张继龙也是熟谙其道。《阿勒坦汗》第84页:
阿勒坦汗第六次征伐兀良哈为1544年,……《阿勒坦汗传》记叙这次征伐说:
青龙年土谢图彻辰汗远征兀良罕,
至而降服兀良罕之莽乞尔丞相、莽海锡格津、波尔合布克等,
使莽海锡格津敬奉守护额真之白室,
于青马年平安凯旋返回家园。
《阿勒坦汗传》记叙的青马年有误,蒙古历的青龙年之后为青蛇年,青蛇年之后为红马年,这次凯旋的时间应是青蛇年底或红马年初,因为在红马年(1546年)春,阿勒坦汗就在丰州滩种地了。
对于《阿勒坦汗传》所记年代的订误,俨然是张继龙自己进行的,其实不然。珠荣嘎先生译注《阿勒坦汗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第48页:
青龙年①土谢图彻辰汗远征兀良罕,
至而降服兀良罕之莽乞尔丞相、莽海锡格津、波尔合布克等,
使莽海锡格津敬奉守护额真之白室,
于青马年②平安凯旋返回家园。
该页“注释②”对这个年代作出考订:
②即甲午年。但自青龙年(甲辰,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至后出白猪年(辛亥,嘉靖三十年)之间,只有青蛇年(乙巳)、红马年(丙午)、红羊年(丁未)、黄猴年(戊申)、黄鸡年(己酉)、白狗年(庚戌),并无青马年(甲午)。此青马年当是青蛇年(乙巳,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或红马年(丙午,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之误。
珠荣嘎先生对古代蒙古历、藏历的研究,在相关学术圈内是人所共知的。其实早在他所译注《阿勒坦汗传》出版前五年,他就发表了有关《阿勒坦汗传》纪年问题的研究论文《从蒙文<阿勒坦汗传>看十七世纪初土默特部的历法》(《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其中,即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说:
其中的青龙年即甲辰年(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后文有白猪年(辛亥,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自莲教徒来投阿勒坦汗的记载,青龙年至白猪年之间,有青蛇年(乙巳)、红马年(丙午)、红羊午(丁未)、黄猴年(戊申)、黄鸡年(己酉)、自狗年(庚戌),并没有青马年(甲午)这一年份。因此,其中的青马年当是红马年或青蛇年之误。
可见,“青马年当是红马年或青蛇年之误”的结论,是珠荣嘎先生研究得出的。张继龙将其据为己有,是典型的“偷意”。遇到此类问题,学界通常的作法是按照学术规范,老老实实地做出注释,对前人的研究成果给予说明。
在复制他人论著的谋篇布局、层次结构方面,张继龙也有动作。《阿勒坦汗》第九部分:
僧格土谢图彻辰汗时期的土默特
一、僧格其人
二、继承汗位与袭封顺义王
三、大板升之战
四、
《土默特史》第二编第七章第一节:
辛爱都隆汗时期的土默特
一、辛爱都隆其人
二、辛爱黄台吉袭封顺义王
三、“大板升之战”
四、
《阿勒坦汗》第十一部分:
博硕克图土谢图彻辰汗时期的土默特
一、博硕克图其人
二、继承土默特汗位与顺义王位之争
三、封王之后的土默特
四、土默特的败亡
《土默特史》第二编第七章第三节:
卜石兔汗时期的土默特
一、顺义王位之争
二、卜石兔汗袭封顺义王
三、封王之后土默特万户的形势
四、土默特万户的衰亡
张继龙对《土默特史》这部分内容结构的“复制”是显而易见的。结构上如此的相似度,除了“偷意”之外,还能是什么呢?
在此,为了掩饰抄袭的痕迹,张继龙又对被他“偷意”的文字进行了“妄改”:他把阿勒坦汗的几个汗号之一的“土谢图彻辰汗”汗号,分别安到了僧格、博硕克图二人头上。在其书关于那木岱楚鲁克的记叙部分中,同样把“土谢图彻辰汗”汗号安在了那木岱楚鲁克头上。在阿勒坦汗身后,僧格、那木岱楚鲁克、博硕克图作为阿勒坦汗的子孙,祖孙三人一脉相承地继承了阿勒坦汗留下的汗位。但是,说他们先后都继承了“土谢图彻辰汗”汗号,却是毫无文献记载支持的臆断。有学者研究指出,对于阿勒坦汗被授予“土谢图彻辰汗”,“虽然对此事的记述不见于汉文史料,而在《阿勒坦汗传》以外的蒙古文编年史中也同样见不到”“土谢图彻辰汗”汗号,更是如此,不要说其他蒙汉文史籍,就是在《阿勒坦汗传》中,也是踪影全无。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对张继龙《阿勒坦汗》一书中的“低级抄袭”、“高级抄袭”等多种抄袭手法作了揭示与评论,同时还初步指出,除《土默特史》之外,乔吉、于永发、李文君、薄音湖、曹永年、珠荣嘎等多位先生的论著也遭到张继龙抄袭。由此我产生了一个感想:如果有更多同行学者到张继龙《阿勒坦汗》一书中去“认领失物”的话,那么,大概会展现出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杂货店”景观吧。
2016年8月13日
张继龙8 月7日短信截屏。
张继龙7月11日短信截屏。
张继龙8月2日短信截屏。
参见张继龙:《阿勒坦汗与土默特》“后记”,第381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
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关于如何认定抄袭行为给××市版权局的答复》,权司[1999]第6号。
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文艺研究》2010 年第 3 期。
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
乌兰译注:《蒙古源流》第6卷,第255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
乌兰译注:《蒙古源流》第6卷,第256页、279页注⑰⑱;晓克主编《土默特史》,第99页;黄丽生:《由军事征掠到城市贸易:内蒙古绥远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14世纪中至20世纪初)》,第167页,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5年。
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
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额尔登泰、乌云达赉:《<蒙古秘史>校勘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
〔日〕永井匠 著,晓克 译:《关于阿勒坦的汗号》,《蒙古学信息》,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