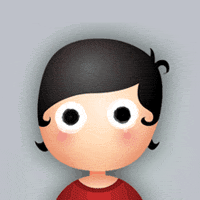擂鼓寨遗址:璀璨大巴山的文明
本文刊登于《中国西部》杂志 2016年6月号
这是一群流浪的人。
他们沿着山脊,顺着河谷,拨开枯草荆棘,穿越历史秘境走来。茫然写在脸上,惶恐揣在心底。
他们究竟走了多少年,我们无从知晓,历史也没记载。命运交给他们的求生法则,就是填饱饥肠,趋安避害。他们顶风露寒,披星戴月,漫无目的,走走停停,寻寻觅觅。哪儿最安全,哪儿就是栖身地;哪儿有野果,哪儿就是落脚点;哪儿有野兽,哪儿就是围猎场。
他们祖祖辈辈不断迁徙。天灾瘟疫跟随他们,部落纷争不时来袭。五千多年前的某个清晨,这座无名小山终于映入他们的眼球。这里一峰独秀,峻峭如锥,三面临崖,视野开阔;小山四周,地势平坦,植被茂盛,硕果累累,鸟兽成群;一泓碧波,潜伏谷底,悄然南去。
居无定所的日子太沧桑,辗转流离的身躯太疲惫。他们卸下惶恐,停下脚步。男人安寨扎营,举石围猎;女人扶乳喂婴,摘果汲水……
1984年3月的某个黄昏,几块石斧重见天日,泄露了这座小山包的密码。随后发掘出土的两万多具石器陶片,宛如破晓晨光,照亮了这座无名小山以及身旁的小村庄,映出了五千多年前那群来此生息繁衍的身影。
这里,就是擂鼓寨遗址,位于四川省通江县春在乡擂鼓寨村。
一次发现,唤醒巴人记忆
擂鼓寨,一处风光秀丽、民风朴质的小山村。相传张飞夜过巴州,曾于此山立寨,擂鼓点兵。明正德初年,蓝廷瑞军曾夜袭其寨,将至,忽闻鼓声大作而惊退。清道光《通江县志》记载:“山有石如鼓,每逢夜深有鼓声自山寨传出,故村以寨名,其地扼通(江)达(州)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
久远传说,地方史料,擂鼓寨,由此冠名这座小山村。
三十年前的几块石头,让擂鼓寨这块其貌不扬的小山头从此拥有了古文化遗址的美名。让人惊叹的是,这处衔接远古人类活动的遗迹,这部穿越五千年时空的百科全书,竟然是被一位名叫赵明皓的本地村民信手拾掇而成。
1984年3月的一天,家住擂鼓寨小学的代课老师赵明皓像往常一样饭后在学校附近的方田边闲逛,脚下一块巴掌大的斧型石片引起了他的注意。随后,他又在擂鼓寨村田边地角捡到了10多块大大小小的“怪石”。粗通史学的赵明皓惊喜不已。通过细心观察,他发现这些石器磨面平整,纹路清晰,大多以磨制为主,器形主要为斧、凿、矛、石球、盘状器等。
“我喜欢研究历史和地理,毕业后就在村里代课,后来被乡政府请去编写《春在乡志》,就把这一发现编进了乡志。”在县城家中,今年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赵明皓谈起那段发现仍然记忆犹新。
。1987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擂鼓寨被专家确认为新石器时代遗址。1990年,。试掘面积100平方米,文化层深3米,共分9层,发掘出土石器、陶器等20685件(片),其中石器及石器半成品812件,陶器19873件(片),所包文化内涵较为复杂,所出陶器的陶质以夹砂陶为主;陶色以黑陶为主,次为橙黄陶、褐陶、红陶,灰陶较少。器物所施纹饰在第1段较为发达,在一件器物上很少单施一种纹饰,而常见两种以上的复合纹饰。纹饰种类主要有划纹、方格纹、绳纹、波浪纹、附加堆纹、凹凸弦纹、戳印纹、篦点文和镂孔等;第2段以后素面陶器增至71%以上,纹饰种类则多由第1段延续下来。流行将器物口沿做成锯齿状或波浪状花边口作风。器物组合主要有罐、尊形器、瓶、盆、钵、杯、碗、器盖等。器物造型以平底器最多,少见环底和圈足器,没有发现三足器和豆类。制法多为手工制作加慢轮修整,多数陶器火候不高。
遗址中还出土了较多的石器和石器半成品,多以磨制为主。器形主要有斧、锛、凿、镞、矛、石球、盘状器等。打制石器数量较少,器形主要有肩石锄、肩石斧、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细石器共出土4件,均为刮削器。
对当地老百姓来说,这些平日里司空见惯的石头并没有改变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轨迹。但在文物专家们的眼里,一块块造型奇特的石片,连同随后出土的陶片,须臾间改写了整个川东北人类活动的历史。这里出土的两万余件文物,不只是古代巴人生产生活的器皿,更是我们人类在通往文明之旅时留下的轨迹。经鉴定,这里的人类活动可以上溯到距今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晚期,连同后来发现的月亮湾等地,其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面积足以纳入当时父系氏族的范畴了。
擂鼓寨遗址,这堆浸润五千多年风雨的陶器石片,这部再现古代人类智慧的进化史,沉酣地下五千多年,一夜之间袒露世人面前,其璀璨夺目的震撼,不止是早于三星堆文化出现,填补了四川龙山文化谱系和类型上的空白,将秦巴山区的文明史上溯了两千多年,更是颠覆了之前史学界对川东北人类文明认知的短见与肤浅,填补了嘉陵江上游乃至川东北文化的空白。
走进现场,再现史前文明
擂鼓寨村位于四川省通江县城东南20余公里处。据资料介绍,擂鼓寨村海拔约740米,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无霜期长,日照时数多。境内擂鼓异峰突起,三面地势平缓,土壤皆以黄色紫泥土为主。地形上呈深丘地带,遗址四周植被较茂盛,山间柏树、白杨树、青杠树及灌木密布,有利于多种动植物繁衍生息。山下通江河及其支流自东北向西南流过。
擂鼓寨遗址主要集中在擂鼓寨西北和南面悬崖下的缓坡地带上,分西东和西南两区。西东区长153米、宽37米,面积5661平方米;西南区长138米、宽22米,面积3036平方米。遗址总面积8697平方米。
一个春光明媚的晌午,在赵明皓老人引领下,我们一行深怀敬畏历史的卑微,驱车绕过盘山通途,直抵擂鼓寨遗址——这块孕育了古代巴人最初梦想的圣地,试图靠近这方活跃巴人五千多年生活的核心。然而眼前的一切,带给我们的不止是欣喜,还有更大的悬疑。
下得车来,放眼望去,一株株俏立地边田角的桃花、梨树,仿佛粉色喷泉。大片大片金黄色的油菜花铺满田间,蚕豆花次第开放,恍如蝴蝶身姿随风蹁跹。
赵老引领我们走过田埂,在一户农家小院停了下来。这里就是赵明皓老人的老家,也是擂鼓寨遗址陈列室及巴文化研究中心。
老人掏出钥匙,打开陈列室的大门,也为我们一行打开了通往早期巴人那段早已尘封时光长河的阀门。
陈列室中,一个个围猎屠兽的石斧,一片片剔骨剁筋的利刃,这些曾经渗透了巴人饮毛茹血的印迹,历经千年岁月打磨与凄风苦雨侵蚀,如今只能静卧玻璃展柜,悄悄舔舐着五千多年来的沧桑。一具具盛食纳水的器皿,一块块突经天火焚化的泥坯,曾经温暖过祖先饮食起居的旧梦,如今早已失去它最初的使用价值,也为我们这些不甘历史沉寂的后人留下了扑朔迷离的迷境。
“这个陈列室是我和家人自筹资金成立的,里面有不同时期的石器、烧结土和陶片。30多年来,我们一共发现了4处石器分布点,收集石器、烧结土800余件,上交文物100多件。”赵明皓告诉我们。
当年带队试掘擂鼓寨遗址的孙智彬认为,擂鼓寨新石器遗址具有典型的巴人文化特征。这些残缺的石器陶片,对普通人而言,不过一堆不值钱的杂碎,但在孙智彬等文物专家眼里,俨然成了刻录巴人历史的标本。这些石器陶片,存在时间漫长,文化内涵较为复杂。主要分布在离河道、水源较远的山顶西坡或较高的台地,这与巴人的生活环境、文化现象相吻合。擂鼓寨等4处新石器遗址见证了古代巴人的经济、文化、生活,已经毋容置疑。
擂鼓寨遗址,这方经由先辈之手、散落时光滩涂、拿捏后人掌心的文化碎片,至今余温犹存。那些五千年前烟熏火燎的碎片,上面阡陌纵横的线条、深浅凹凸的斑痕,是在张扬着绘画史上的美,还是启迪着我们这些迷失了方舟的子孙?那些残破的石斧石矛,既有早期石器粗犷的证据,又有后来精细加工的遗迹,这些无不证明擂鼓寨遗址,曾经历经了多少岁月的打制和磨砺!这段旅程,多少块石斧石矛深埋地下,多少片器具散落他乡,谁人能知,又有谁来唤醒?
回眸历史,谁是最早的巴人?
回到篇首,再提那群流浪的人。
巴人,史学界主流倾向于分布在今川东、鄂西一带。他们不但骁勇善战,而且能歌善舞,极其乐观,是古代一支“神兵”。他们在荒莽的大巴山、秦岭中,在极为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下,自强不息,世代繁衍。他们斩蛇蟒、射虎豹、猎牧捕鱼、垦荒种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这对川东地区,特别是大巴山一带经济文化的开发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至清朝,川东北及川东地区历史上曾有五次移民迁入。由于战争、瘟疫和天灾等原因,川东北及川东地区历史上曾出现过饥荒无人、尸横遍野、群虎白日出游、賨人几乎灭绝的惨景。为填补战争死亡、瘟疫死亡、天灾死亡形成的空缺,秦朝、西晋、北宋、元末明初、清朝曾五次移民入川。这五次移民的迁入,既促进了川东北及川东地区土著居民与汉民族的同化,又加快了当地的开发步伐。
纵观早期人类活动踪迹,巴人源自何方?何时入川?史学家们迄今喋喋不休,尚无定论。但对时间跨越节点的关注,似乎一直讳莫如深。
如果手持时间指针,溯回历史源头,我们或许能找到这群人的蛛丝马迹。
巴人最早步入今人主流视线,多以重庆渝中区为据。他们大约4000多年前就已在四川东北部和长江、嘉陵江、汉水流域散居,这就是那支骁勇善战、勤劳朴实、以狩猎捕鱼和耕作为生的巴人。但在两千多年前却突然神秘地消失了,只给文献资料留下了无从考证的神话传说,以及后人无尽的想象空间。
另一处相对集中的巴人遗址当数罗家坝文化遗址,距今有3000到4700年历史。该遗址地下保存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和东周时期的墓地遗存。遗址堆积甚厚,约在2至3米间,年代跨度较大。遗址早期地层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陶片中有夹砂褐陶的花边口沿、折沿罐口、喇叭口罐沿、尖底器等川东北地区同期常见的出土物。发掘者认为,该遗址与川北通江擂鼓寨、巴中月亮岩、峡江忠县哨棚咀一期、奉节老关庙下层、陕南李家村文化等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罗家坝遗址面积约50万平方米,是“1999年四川省十大文物工作成果”,。
上述遗址,皆以巴文化中心自居。但他们似乎都刻意避开了对时间的追溯。
从地域文化看,擂鼓寨遗址虽然地处古代巴的地域位置,但它比巴文化的历史更漫长,并非狭义巴文化的遗存,而是巴人史前土著文化的遗迹。通过碳十四标本的测定,擂鼓寨遗址当在新石器时代范围内,其绝对年代或许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早期阶段,或者更早,并较之四川境内业已发现的其他属于当地土著文化系统(火溪除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具体年代上大略偏早。
从绝对年代上看,擂鼓寨文化早于宣汉罗家坝和重庆渝中区两地而存在。重庆渝中区文化遗址上溯历史大约在4000多年,晚于擂鼓寨遗址1000多年;罗家坝文化遗址也晚于擂鼓寨数百年而盛。
从出土文物看,亦可佐证擂鼓寨遗址早于上述两地文明。
可以想象,擂鼓寨早期人类活动时期,其生产生活用具皆以石器或泥坯为原料,且技术单一,加工工艺相对粗糙,远非宣汉罗家坝和重庆渝中区可比,更无青铜时代冶炼技术。
笔者以为,擂鼓寨人类当属罗家坝和重庆渝中区先民。早在周朝以前,这批先民居住在今甘肃南部甚至以北的天山,后一路南下,一支迁到武落钟离山,即今湖北长阳西北一带;另一支翻秦岭、入巴山,在通江、南江一带滞留数百年,后继续南下,在罗家坝以及川东其他地区创造了更为先进的文明。秦灭巴以后,巴人的一支迁至今鄂东,另一支迁至今湘西,构成武陵蛮的一部分。留在四川境内的部分叫板楯蛮。南北朝时因大量迁移,大都先后与汉族同化。
巴人故里之争,皆以规避时间而论,说到底都是狭隘的地域文化之争。
巴人行踪,期待科技进步
擂鼓寨遗址,一曲幽远的绝唱,一段独吟大山深处的文明,历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喧嚣,促成多少术业专攻、高位绝顶。一夜东风的花露,依然没能润泽山民碗里的米香。唯有你,矗立嘉陵江源头,坐拥四方山水,怀抱一轮明月,偶尔睁眼,撒落几块断片,安慰着与她同样孤独的老人——那位最初发现、呵护她至今的守护者。
一湾秋水,俯首南归,汇入涛涛嘉陵江。通江,这块古属巴国的南蛮,在历史长河的滩涂一路跌撞,踉跄走来,有过辉煌,也曾冤屈。但相较擂鼓寨数千年来的寂廖与坦然,通江的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那些承载了先祖希望与梦想的石斧石矛,历经尘掩土埋,待到重见天日,早已支离破碎、溃不成形,失去了当初的使用价值。唯有时光的看护者,在几十年的守望中,以一种不舍的姿势,躬身拾放于精心擦拭的展柜。她的安然,宛如巴山秋月,清澈着这方水土固有的宁静;在盈亏之间,讲诉着这方水土曾有过的辉煌和传奇,等待全景重现那天的来临。
如果说银耳之乡和红军文化是通江两扇大门的话,那么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地平线上,回眸身后七千年灿烂的文明,擂鼓寨遗址已悄然推开历史大门——这缕混沌初开的蓓蕾,正翘居绵长古道米仓南麓,迎着新世纪的复兴之光,华丽绽放。她正卸下五千多年风沙掩埋的沧桑,以其少女褪稚的初颜、不施粉面的光洁与灿烂,长歌舞袂通江南大门,流波顾盼姗姗来迟的兄弟姐妹,笑纳世人的惊叹与敬仰。
前些年,在擂鼓寨周围的土地上,又陆续传来了大量石器陶片出土的消息,其中当数广纳境内的铜钵山、麻石五香庙两地最负盛名。据初步考证,当与擂鼓寨文化同一时期。连同之前巴中月亮湾遗址的发掘,进一步衔接了这段失落的文明。这些发现,不仅将擂鼓寨遗址的范围扩大到了方圆几百平方公里,更是抚慰着擂鼓寨文化这桩孤案悬立的困惑。
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科技日臻完善,擂鼓寨遗址终将卸下千年孤独,拥抱巴人——那些散居四方的兄弟姐妹!
(来源:《中国西部》杂志社 文·图\蒲江涛 详见 《中国西部》杂志2016年6月号)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转载请至后台留言申请授权,否则将按《微信公众平台关于抄袭行为处罚规则的公示》处理
如果您也刚好喜欢我们的内容,
长按二维码,选择识别就可以关注哦!
让我们成为您的口袋读物,
伴您享受阅读的妙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