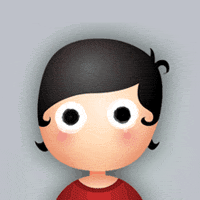景天魁:难解的反贫困难题——进城打工的经济收益远抵不上其他损失 贫困之殇
▼
编辑部推出三大措施扶持青年学者
活动进行中(点击蓝色标题可查看)
甘肃康乐县的人间悲剧无需复述,每一次提及,都仿佛重现了残酷的场景,令人心头发颤,愤懑不已。痛斥与诘问,只是逞一时之快,也不应停留在悲惨的表象中投射自我焦虑。我们需要的是,冷静下来,理性思索,解开“为面包犯罪”的社会之困。今天,为您奉上景天魁研究员、朱力教授等人的文章。景天魁研究员指出,在进城务工人员日益受到关注之时,留守老人、妇女、儿童却仍是“被遗忘的角落”,缺乏必要的社会关怀和社会保护,社会政策在许多方面付诸阙如。贫困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它还体现在社会、文化、精神和心理等方面。
甘肃康乐县的人间悲剧无需复述,每一次提及,都仿佛重现了残酷的场景,令人心头发颤,愤懑不已。痛斥与诘问,只是逞一时之快,也不应停留在悲惨的表象中投射自我焦虑。我们需要的是,冷静下来,理性思索,解开“为面包犯罪”的社会之困。今天,为您奉上景天魁研究员、朱力教授等人的文章。景天魁研究员指出,在进城务工人员日益受到关注之时,留守老人、妇女、儿童却仍是“被遗忘的角落”,缺乏必要的社会关怀和社会保护,社会政策在许多方面付诸阙如。贫困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它还体现在社会、文化、精神和心理等方面。
难解的反贫困难题——进城打工的经济收益远抵不上其他损失
景天魁 |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原题《社会政策的效益底线与类型转变——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反贫困历程的反思》
原载《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0期
本微信有删节
社会政策研究有很强的应用性和针对性,但不是应急型。应急型社会政策的主要特点:一是被动应付,问题出来了,摆在眼前了,临时对策;二是只追求眼前效益,不顾及长远效益。
与此相对照,储备型社会政策是指,基于预测预判,主动应对;有时间和有可能顾及长远效果,并且讲究诸种相关政策的综合配套,从而具有前瞻性、综合性和长效性。
要提高社会政策的有效性,顾及它的长远效果,关键是要重视效益评估。对社会政策而言,进行综合的效益评估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也就是说,一项社会政策的即时性效果也许不明显,但长期效果总是会表现出来的,而且一般是可测量的;从不同维度看,效果可能有差异,甚至正相反,但综合地看效果也有统一性。
社会政策不能只重视短期效益,更要重视长期效益;不要局限于某一方面的效益,更要重视综合效益。
因此,社会政策必须守住效益底线——其效益的综合评估不能为负。综合评估既包括近期效益,也包括长期效益;不能为负是指一项社会政策的前期效益和后期效益之间、不同社会政策的效益之间,即使有相互抵消的情况,但总体效益不能小于零。
经验表明,应急型社会政策由于过于追求眼前效果,容易导致长期效益和综合效益为负,因此社会政策要从应急型向储备型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贫困历程和效果
国内外文献普遍认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在反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以往的30多年里,中国的减贫占全世界减贫总成就的2/3。
1978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高达2.5亿人,贫困发生率达30.7%。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贫困人口持续下降,到2005年底已降到2365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为2.5%。
在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中国大陆的反贫困事业进入了新阶段。虽然对于这个新阶段应该怎样概括,学术界有不同见解;但有一个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大家都看到,以经济增长消除贫困的效果趋于递减。
数据分析表明,1978~1990年,我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减少贫困人口1320万人;1991~2000年,这一数值下降到380万人左右;进入新世纪以来,则进一步下降到100万人。
表现在年度数据上,中国农村贫困规模虽然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但减贫速度明显放慢。1979~199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平均每年减少1375万,1991~2000年平均每年减少529.1万,2001~2005年平均每年只减少168.8万。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关于经济增长与减缓贫困的关系,有计量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对贫困发生率下降的影响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趋小。在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农业产出比例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导致贫困发生率减少0.487个百分点。农业增长得越快,贫困发生率下降得越快。
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非农收入对减缓贫困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减缓贫困将越来越依赖于专门的扶贫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政策对减少贫困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直接,因此,社会政策本身的效益就越来越重要。
从社会政策本身的效益角度看,不仅新阶段反贫效果下降与社会政策有关,有些社会政策不当还成为导致某些贫困发生或延缓的原因之一,或者即使没有造成新的贫困问题,也引发了一些其他社会问题,间接地增加了反贫的难度。
经过一个较长时段的观察可以发现,有的地方持续20年反贫,不见效果,贫困帽戴得很牢;有的地方甚至越反越贫(如部分西部农村);有的地方出现了新的贫困群体和贫困问题。
因此,要及时研究贫困群体构成、致贫原因、反贫效果的变化,适时调整反贫困政策,改变反贫困思路和策略。
为此,我们需要加强对社会政策现有效益的评估和未来效益的预估。这再次提示,社会政策由应急型向储备型转变是必然趋势。
四个维度下的社会政策效益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中国大陆开始普遍推行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中国累计少生人口达3亿人,节省相关开支3600多亿元。与此同时,各级政府把计划生育政策同扶贫开发结合起来,向计划生育贫困家庭提供各种优惠和免费服务,帮助他们尽快脱贫致富。在这个意义上,计划生育政策可以看作一项反贫困政策。
然而又过了10年,在人们高度肯定计划生育政策的反贫困效果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一个不期而至的后果——失独家庭。据调查,截至2012年底,我国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庭。有专家预估,每年这样的家庭还会新增7.6万个。
计划生育政策在缓解人口众多的压力、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仅仅30年后,就迫使社会、家庭和个人支付巨大的成本。这个后果,是当初制定和推行这项政策时没有或至少没有充分预料到的。
这项政策的近期和长期效益的差异提示我们,对于一项社会政策的效益,只看到近期效果,忽视长期效果;或者只从一个角度看,例如只从人口数量或者经济效益看,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高度兼顾社会政策的近期和长期效益,预防发生效益递减甚至跌破效益底线的风险。
传统的城市贫困人口是以“三无”对象(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无法定抚养人的社会救济对象)为主。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日益增多,除了“三无”对象这一特殊人群外,主要来自因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调整而形成的下岗失业群体,以及资源枯竭型城市具有劳动能力的居民,部分退休较早仅依赖很低的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流入城市的部分农村人口。
上述城市贫困群体的产生,固然有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有家庭与个人方面的主观原因,但是主要原因是政策本身的偏差和政策执行过程的偏差。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企业改革,导致“在职”职工就业没有着落,退休职工养老金无处领取,有病的职工拿着一大把医疗费单据无处报销。尽管有很多理由为企业改革的必要性、某些问题的难以避免性辩护,但这一政策也使得贫困不再被看作主要是个人和家庭原因(生病、残疾、天灾人祸等)造成的,而被看作是社会和政策原因造成的——这几乎成了对贫困的一种普遍的认知模式。
面对突如其来的下岗“洪水”,不得不采取的应急政策是所谓“三条保障线”(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这些“保障”层次和水平都很低,而接受这种最低保障的对象是享有“国家主人翁”地位的下岗职工,许多昔日的生产能手、劳动模范从万人仰慕顷刻间变成备受冷落的对象,这种心理创伤是难以承受的。这时,他们不再把贫困仅仅理解为一种经济现象,而是理解为包括社会权利、社会地位在内的综合问题。
人们由此扩大和深化了对贫困的理解。表面上,贫困表现为由于收入水平低而难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实质上,贫困是由于不具备与他人相同的权利、能力以及机会去获得体面的生活。
以上“改变”已经历史地发生了,留给社会政策的不是功过的评说(那是个人和历史关心的事情),而是经验教训的吸取:在追求经济效益时,我们应该估计到为此付出的社会成本;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该同时制定配套的社会政策。
城市贫困人口中还有一个新群体,被称为新的“三无对象”。在城市生活中,他们是“流动人口”、“外来人员”、“陌生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是特殊的城市贫困人群——没有土地(离开农村),没有固定工作(仅属于临时工),没有与城市职工和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他们既不具有城市居民身份,又脱离了原来农村的社会支持网络,往往游走于城乡之间。
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相较于计划经济时期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的那种政策,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但是,正当农民进城务工政策充分显示出正面效益,不可忽视的负面效益也凸显出来。客观上是由于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根深蒂固,一时难以撼动;主观上是由于我们过分重视农民工给城市和个人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忽视了本应给予更大关注的社会效益和社会问题。因而,不论是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角度,30多年来积累了一些难以破解的社会难题。
一是社会公平难题。农民工因为户籍的限制不能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只能参加标准相对很低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养老保险;这两项制度分别迟至2003年和2009年以后才陆续建立起来,且由于农民工常年在城里务工,医疗服务的可得性其实很差,养老保险对年轻的农民工来说更是遥不可及。如遭大病或不测之灾,即使贫困,也难以获得城市的社会救助,不能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等基本福利待遇。这些社会权益的缺失成为流动人口贫困现象的重要根源。
二是社会认同难题。不公平,也就难以形成社会认同。许多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多年,仍然缺乏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主要原因是制度性和政策性排斥所致。流入地政府对本地居民就业和再就业提供特殊优惠政策与措施,造成了竞争环境的行政干预和事实上的就业歧视;流动人口在居住、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受到长期的制度性限制,农民工及其子女客观上被置于“二等公民”的地位。
三是社会整合难题。缺乏社会认同,也就难以形成社会责任感,难以建立人际信任,这样的社会就很难实现整合。而难以整合是社会治理的最大难题,破解之道就在于需要政府、社会、社区、家庭和个人分别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建立起包括财政、就业、法律、教育、交通、住房、工会等综合的社会整合机制。
近年来,进城务工群体已经受到了社会关注,那些留守农村的老人、儿童和妇女,却经常处于“被遗忘的角落”,缺乏必要的社会关怀和社会保护,社会政策在许多方面付诸阙如。
子女不在身边的留守老人成为日益庞大的一个特殊群体。大多数留守老人生活清苦,饮食简单,不仅承担着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担负起抚养教育孙辈的重任。而留守老人本身是弱势群体,农村社区普遍缺乏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和精神慰藉等基本的养老服务。近年来留守老人率明显升高。
由于父母进城打工,留守农村无人照管的儿童人数也在不断增多。他们失去父母庇护,身心、学习、成长都面临着失管、失教和失衡;其在个性心理上往往表现异常,如性格内向、孤僻、自卑、不合群;脾气暴躁、冲动易怒;极易发生犯罪和越轨行为。
至于留守妇女,除了独自支撑门户、抚育子女以外,还要承担几乎全部农活,往往身心疲惫、精神焦虑。因夫妻长期分居,家庭发生矛盾甚至破裂的比例也较高。因此,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第二代农民工夫妻同时外出打工的明显增多。
“留守”是“进城”的另一面。进城务工在经济上可能给家庭增加了收入,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脱贫的意义。但是,贫困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它还体现在社会、文化、精神和心理等方面。很可能经济上的收益,远远抵不上其他诸多方面的损失。
这倒不能因此就否定进城务工政策本身,而是应反思其应该具有的整体性。流动就业会触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要同时考虑到就业政策、培训政策、分配政策、户口政策、居住政策、家庭政策、子女政策、购房政策、福利政策、学校政策、就医政策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对流动就业及其影响到的相关群体提供政策保护、政策预防、政策跟进以及政策创新。
社会政策类型转变的必然性与可行性
对于长期被认为取得巨大成就的社会政策,我们现在所做的反思,不是重新评价,更不是全盘否定,而只是从总结经验的角度,着重于综合效益的评估。
许多社会问题的涌现或者是政策供给滞后,或者是社会政策缺失和缺陷的必然结果。我们在充分肯定应急型社会政策曾经发挥的正面作用、充分理解它们当初出台的情景合理性的同时,对社会政策尤其是其社会效益的公平性、可持续性和科学性,从总体上加以反思刻不容缓。
实现社会政策从应急型向储备型转变具有必然性,也具有可行性。
第一,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不能再沿袭追求温饱阶段的反贫困策略和社会政策。不光是要提高贫困标准,更要重视致贫原因、贫困对象的变化;不能只重视绝对贫困,更应该预防和消除相对贫困;不能只关注物质方面的致贫因素,更应该关注精神方面的致贫因素;不能只追求短期的反贫效果,更要追求长远的、根本性的反贫效果。
第二,只有从应急型向储备型转变,才可能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效益评估,尤其是进行中长期效益评估。反贫困要有战略构思:不要过分把它看作“政绩”,要科学地、理性地看待贫困。不要太着眼于消除贫困的现象,而应重视消除产生贫困的原因。储备型社会政策的主攻方向应该是尽可能地消除导致贫困的根源。
第三,社会政策研究只有重视效益评估特别是中长期效益评估,才可能获得较优的综合效益。在不具备基础性条件情况下的政府干预式反贫,重点应放在改善和培育基础性条件(包括改善生活和生产条件,加大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更重要的方面应该是发展教育)上,而不是追求眼前的反贫效果。
第四,社会政策要实现从应急型向储备型转变,预防发生效益递减甚至跌破效益底线的风险,就必须在政策研究的功能定位、研究体制和范式、研究方法等方面有一系列调整和提高,才可能达到预期目标。在功能定位上,,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但不是为文件作注脚;在研究体制和范式上,要真正向现代智库转变,发挥智囊作用,特别重视决策前的预案论证、决策中的参与咨询、决策后的跟踪评估,切实实施全程的决策支持;在研究方法上要提高科学化水平,重视社会实验,运用模拟与仿真等科学技术手段,加强理论基础和经验论证,较大幅度地增强社会政策的科学性,提高效益水平。
END
人文社科学者的平台
《探索与争鸣》
唯一官方微信平台
联系电话:021-53060418
投稿邮箱:tansuoyuzhengming@126.com
版权所有。欢迎个人转发,媒体转载请联系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