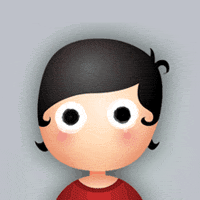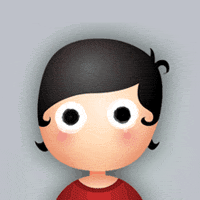讲座综述丨Chinese Temple of Art:从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看美国在1930年代的中国艺术收藏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0-11-20 09:31:04
2016年6月14日晚,。此次讲座由美国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副教授林伟正主讲,、教授郑岩主持,题目为:“Chinese Temple of Art:从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看美国在1930年代的中国艺术收藏”。图01/Building a Sacred Mountain: The Buddhist Architecture of China's Mount Wutai林伟正先生于2006年获得芝加哥大学艺术史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中古时期美术史的研究,涉及、建筑和墓葬等领域。林伟正于2014年出版了专著《营造圣山:中国五台山的建筑》(Building a Sacred Mountain: The Buddhist Architecture of China's Mount Wutai),目前正在进行有关“中国建筑表演性的历史”(History of China's Performative Architecture)的研究,旨在探讨中国建筑塑造的空间概念及其诱发的想象,突出建筑在历史中的主体性。在这次的讲座中,美术和建筑空间均是关键词。图02/1950年代的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大中国展厅在讲座的开始阶段,林伟正先生首先介绍了自己早年间在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以下简称“纳尔逊美术馆”)的工作经历。借助在该馆整理档案的机会,他开始关注美国的东方艺术藏品,尤其对来自北京智化寺的明代斗八式蟠龙藻井产生了兴趣。面对远渡重洋的中国寺庙建筑的精美构件,在发现无法简单地通过对比文献和图片进行解读时,林伟正希望追溯文物原本的空间环境并梳理其流失海外的详细过程。智化寺是北京城区保存至今最为完整的明代寺院,寺内如来殿(阁楼建筑,二层为万佛阁)和智化殿的藻井于1930年分别为纳尔逊美术馆和费城美术馆购买出境。2008年,林伟正来到智化寺,,但是阴差阳错地使用了纳尔逊美术馆提供的如来殿藻井图像,这一现象启发他思考新的问题:文物实体及其原始场所之间的关系以及博物馆对艺术品身份的建构。图07/智化寺智化殿藻井部位错误配置了如来殿藻井图像(2008年)纵观美国博物馆对东方文物的陈列,不外乎以下几种形式。其一,使用常见的橱柜或展台,因此使得一些本来不被认为是艺术品的物件成为被欣赏的对象;其二,进行场景复原,即尝试重建物品原本的语境,如波士顿美术馆1910年仿建的日本佛殿。另外一种则将更为完整的建筑本体作为展示对象,1940年代费城美术馆即整体性地搬迁并恢复了来自北京的一座明代民居。不管是哪种方式,物体的移动或重组带来的错置(displacement)仍然造成展览对象的身份转变。图09/美国博物馆对中国文物的场景复原展示(费城美术馆)20世纪早期,大型古代遗物散失海外的现象在中国普遍发生,林伟正认为对这一历史过程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观察。一、破碎性,当物品被取走后原来的语境即变得支离破碎;二、“伤疤”的出现,如智化寺智化殿内代替藻井的照片;三、新语境的产生,移动之后的物品在新的环境下得到包装,身份随即发生改变——透过纳尔逊美术馆的例子,可以清楚地读出上述三种概念。纳尔逊美术馆位于美国中部腹地的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于1933年12月对外开放,外观采用了当时流行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样式,但是内部却容纳了一个中国式的“佛殿”——东方空间的生硬嵌入多少让人感觉到怪异。图10/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开馆之初入藏的五、六千件中国艺术品大多直接购买自中国本土,占据纳尔逊美术馆藏中国文物总数的70至80%。1930年代,购藏中国文物在美国达到了高峰,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文物的价格在当时大多较为低廉;另一方面,购买文物是“大萧条”背景下一种保险的经济投资方式。在林伟正来看,相比收藏史更加值得美术史学科关注的是对中国文物的处置、改造和重建行为,以及隐藏其中的、作为物质性存在的文物与文化概念之间的关系。纳尔逊美术馆的中国佛殿中除了藻井,,以及6世纪的菩萨造像和清代门板,它们被拼揍在一起,给人一种中国风格的印象。《堪萨斯城星报》(The Kansas City Star)曾经如此评论:“昨日,中国古老深沉的寂静就在展厅的佛殿中,从这些3000年来伟大的作品之中,这个不朽民族的美与光荣似乎比起博物馆正门外的大马路还来得靠近我们”——事实不完全像诗意化的文字所说的那样,这一空间其实并不真实。上述报纸同时刊发了一张手绘图,画面中透过门扇可以看见壁画和藻井,还有两位背对着画外正在观赏艺术的西方人。图13/《堪萨斯城星报》插图“从大中国展厅观看佛殿”现代博物馆在“文物”(cultural objects)转变成“美术作品”(fine art)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文物在西方博物馆的出现却具有额外的含义。讲座主要关注的是,在改造现象之下,人为性想象的发生以及其技巧与手段,主讲人随后从几个方面详细论述了这一问题。首先是纳尔逊美术馆东亚部主任、后来的馆长劳伦斯·西克曼(Laurence Sickman, 1907—1988)的收藏活动,其次是中国历史古物(或文物)身份的转折,最后是1930年代购买取得中国古物(或文物)的过程,由此希望揭示纳尔逊美术馆中国佛殿组成和展示的全过程。图14/劳伦斯·西克曼(Laurence Sickman)早至19世纪末,中国文物就伴随着西方人的购买和战争掠夺而外流,中国的古物开始被作为艺术品而收藏。与此同时,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也开始重新认识古物,他们将其视为国粹的物质表现,此前不受重视的陶器、铜器、造像和印章开始被广为收藏。罗振玉建立了一种新的分类方式,将古物区分为书画和器物,分别具有二重空间和三重空间的不同遗存形式,并且认为它们是中国文化和历史的遗产。在官方层面,民国北洋政府于1914年在北京紫禁城内设置了古物陈列所,对公众展出贴有标签的清代宫廷文物,1924年建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次年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然而,此时的西方人认为中国人并不具备理解本国文物意义的能力,而是倾向于自以为是地将中国文物取走,作为其所认为的世界性文明遗产的一部分。此外,清朝皇室成员则将清宫文物视为自己家族的私有物产——可以看到,在早期,关于“文物”的多元化观念同时并存。图16/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图17/华尔纳盗走的敦煌彩塑,原位于莫高窟328窟,现藏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西克曼在1920年代末期来到中国,并持续活动至30年代,与他关系密切的收藏家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 1881—1955)是哈佛大学教授,同时,受聘于纳尔逊美术馆并成为东亚艺术代理人,曾因盗走甘肃敦煌莫高窟328窟的供养菩萨而恶名昭著。面对前所未有的文物买卖形势,华尔纳的愿望是建立栩栩如真的中国厅。1838年,费城的一家古玩店和1876年的世界博览会中国馆已经模仿了中国建筑景观,但是华尔纳希望以真实构件组建更大的建筑空间。为此,他在中国进行了实地考察,寻访了残破的古代建筑并对其精彩的细节赞赏不已,但是由于皇家建筑过于高大,他的设想未能实现。图18/Nathan Dunn,中国式佛殿,费城,1838年。在放弃原有想法的同时,华尔纳收到德国古物商提供的智化寺如来殿藻井的照片。在西克曼与建筑史家古斯塔夫·艾克(Gustav Ecke, 1896—1971)赴实地查看之后,博物馆决定买下这件藻井。在留存的拆解藻井的照片中,我们看到文物被移动和重新编排的过程,艾克专门设计了一张表现陈列效果的手稿,草图中对藻井的构件进行了重新排列,并将整体空间定义为存放“宝藏”的场所。1931年,民国政府行政院公布了《古物保存法》和《古物保存法施行细则》,规定包括建筑在内的文物均不允许出境,西克曼等人因此加快了行动。图25/纳尔逊美术馆“中国佛殿”设计图稿,艾克和西克曼绘制。在1932年中国营造学社刊布的《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中使用了艾克拍摄的照片,暗示着中西方学者之间的微妙联系。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骨干之一梁思成在哈佛大学求学时修过华尔纳的课程,与西克曼也存在交集,而艾克则是学社第一位外籍会员,而另一位学社核心成员刘敦桢后来帮助费城美术馆组装了智化寺藻井。因此,中国和西方学界之间的界限自始至终都不是非常严格。因此,在中国营造学社调查智化寺时,他们深知藻井流失的具体情况。与此类似的情况也反映于1935年出版的《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使用的广胜下寺照片:1927年,鉴于佛寺的颓败,僧人出售了后殿西山墙壁画《炽盛光佛佛会图》,进入纳尔逊美术馆,而东山墙壁画《药师佛佛会图》则入藏纽约大都会美术馆,梁思成在去往广胜寺之前已经掌握西克曼的照片,可见当时的中国学者也处在一种时代的矛盾之中。图28/纳尔逊美术馆“中国佛殿”模型,卢芹斋制作。图29/纳尔逊美术馆“中国佛殿”模型,卢芹斋制作。图30/纽约大都会美术馆拼装广胜寺下寺后殿东壁壁画《药师佛佛会图》图31/纽约大都会美术馆拼装广胜寺下寺后殿东壁壁画《药师佛佛会图》图32/纽约大都会美术馆藏广胜寺下寺后殿东壁壁画《药师佛佛会图》现状关于广胜寺下寺壁画,不得不提及著名的法国华裔古董商——卢芹斋(C. T. Loo, 1880—1957)。他制作了一套带有缩小版壁画以及天花和门板的模型,将其展示给纳尔逊美术馆,承诺馆方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展示方案:“我可以跟您保证……在完成后,整个展厅将非常吸引人,并且跟博物馆的美术品互相协调,您将会带给一般大众莫大的助益。”博物馆欣然接受了这个提案,因此产生了后来的改造,壁画被拆解成一百多块运送至美国,而在最近的扫描中,可以看出至少有15至25%的部分是经由卢芹斋修复的。门板被按照实际的展厅高度进行了修改和补充,梁柱和雀替与壁画边界相配合,但是壁画的陈列方式却与原本的空间配置大相径庭。通过极尽细致的保存手段,西方学者掩盖了其行为的不正当性,同时自认为掌握了占有中国文物的权力。相似的心态表现在1935至1936年于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上,中国专家的意见遭到否定,西方人对参展文物进行了重新鉴定。图33/卢芹斋对广胜寺下寺后殿西壁壁画《炽盛光佛佛会图》的修复图34/卢芹斋对广胜寺下寺后殿西壁壁画《炽盛光佛佛会图》的修复图35/卢芹斋对广胜寺下寺后殿西壁壁画《炽盛光佛佛会图》的修复“破碎”的概念还鲜明地体现于纳尔逊美术馆收藏的龙门石窟北魏浮雕《皇后礼佛图》,与西克曼早期拍摄照片相比较,可以看到最终呈现的展示对象经过了较大程度的修复和美化。因而,纳尔逊美术馆所构建的中国艺术品殿堂,实际上只是表现了一个想象中的中国,陈列的文物与原始语境之间有着不可弥合的鸿沟。图36/纳尔逊美术馆藏龙门石窟宾阳中洞浮雕《皇后礼佛图》的修复图37/纳尔逊美术馆藏龙门石窟宾阳中洞浮雕《皇后礼佛图》的修复在讲座的最后,林伟正提到这样的一个故事:梁思成参加完194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举办的“远东文化和社会”(Far Eastern Culture and Society)学术研讨会后,特地参观了纳尔逊美术馆,他虽然没有对中国营造学社在调查中涉及的智化寺藻井作出表态,却惊艳于《皇后礼佛图》和《炽盛光佛佛会图》的重新拼装——梁思成的态度或许表明,在他眼中虽然这些物品不再保存于中国,它们的文物身份依然延续。图38/梁思成参加1947年普林斯顿大学“远东文化和社会”学术研讨会讲座结束后,主持人郑岩教授进行了总结:考古学定义了“遗物”和“遗迹”的差别,呼应了文化遗产中“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的区分,讲座中提及的智化寺藻井体现的恰恰是对不可移动文物的移动。因此,纳尔逊美术馆中的“temple”可能有两重意义,一种是实质的建筑意义,一种则是隐喻性的,后者一方面是粗暴的处置、改造与重建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文物所象征的文化经过转译后的状态。西方的博物馆建筑嵌入了中国建筑的组成部分,使得西方艺术史的结构中纳入了中国艺术,同时在中国文物被转译的背后,西方的美术概念也被转译到中国并一直影响到今天。在提问和交流环节,在座师生就历史上文化遗产的文化接受和价值评判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对话,林伟正先生也强调了他在研究中秉持的面对历史问题的冷静态度。对西方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的史实的梳理在今天看来已经成为学术史的一部分,重要的是分析历史发生过程中的观念变化及其在历史上造成的影响。图41/纳尔逊美术馆藏广胜寺下寺后殿西壁壁画《炽盛光佛佛会图》美术史研究需要面对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和现代艺术等具体对象,在材料和方法不断更新的同时,学科意识和学术源流作为构成美术史学史的重要方面,也应当是学界关注的重要对象。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很多术语、概念和范式无不出自其中,林伟正先生以纳尔逊美术馆为个案,通过对美国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的研究,梳理20世纪初期中国文物流传和收藏的历史脉络,最终将目光投射到文化观念和学科范式的理论高度,其方法和结论均令人印象深刻。,由人文学院主办,主要邀请美术史、考古学、建筑学和文物保护工程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展示、利用、教育等议题举办讲座,理论性与技术性并重,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