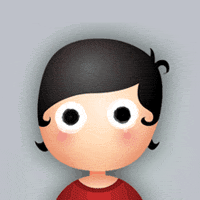初闻钟山石窟之名,我甚感陌生,继而有些惊诧:对这个国宝级的石窟,我竟然闻所未闻,这实在令人汗颜。作为一个艺术爱好者,我曾有过数次寻访石窟之旅,敦煌、云岗、龙门、麦积山四大名窟不必说了,其他一些散落各地的石窟,若甘肃的炳灵寺、天梯山;山西的天龙山;河北的响堂山;四川的千佛崖、禹迹山;云南的宝石山;重庆的大足石刻;新疆吐鲁番伯孜克里克千佛洞等等,我都曾一一探访过,自问对中国的石窟艺术并非孤陋寡闻,然而,偏偏对这个1988年就已名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钟山石窟,我却一无所知——怎么会这样呢?
6月17日,就在到达延安子长县的当天,我给一位熟识的敦煌学博士打了电话,请教关于钟山石窟的情况,孰料这位同事对此也并不知情。我由此悟到:这座开凿于北宋年间的古老石窟,隐匿于陕北的黄土高坡太久太久了,以至于岁月淹沦其名,偏远尘封其迹,于是,走进这古老石窟,目之所及,吉光片羽,探微发奥,条分缕析,哪怕只是掀开钟山石窟神秘面纱之一角,能让更多的朋友了解这个曾被喻为“第二莫高窟”的边塞佛国,则余愿亦足矣。
以陕北红军创建人之一谢子长的名字命名的子长县(县府为瓦窑堡),原本叫作安定县,旧县衙设在安定镇。镇外二里处,有一座并不险峻的小山,形状酷似一口倒扣的铜钟,故名钟山。钟山脚下,秀延河穿流而过,一座新建的大桥将安定镇与钟山石窟连为一体。
走进钟山石窟,如同游历一个立体的时空画廊,各个时代的遗迹叠印于石崖间,令人如同与各个朝代的先人对视交流——唐人的题刻被宋人的造像所覆盖,明代的碑碣与清代的牌坊相呼应。由此切入,我们仿佛窥视到此山此寺的悠久历史和岁月沧桑。
钟山石窟开凿于何时,一直众说纷纭。在明代一通《重修万佛岩寺记》记载,早在晋太和年间(公元366至370年),钟山就已开凿了石窟,此后千百年间又经过多次大规模的增修扩建,才逐渐形成规模,蔚为大观,成为陕北最大的石窟群。 现存石窟造像的主体部分为北宋英宗治平年间所开凿,这一点在第三窟顶部的题记中得到了确证:“治平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同州界安定堡百姓张行者发心打万菩萨堂。”明代的一通《增建万佛岩塔记》援引其说:“安定在秦汉时为塞北沙漠地,宋因为堡,元升为县。其城东一里许,志曰‘钟山耸秀,为邑胜之第一景也。’寺名万佛岩,有宋治平四年僧行者偕石工王信辈依山相地凿石为洞,万佛森列,八柱挺立,盖将与天地相为终穷者也。”![]() 钟山石窟群,现存大小洞窟18座,目前发掘了9座,但开放参观的只有6座。石窟的精华部分集中在第三窟,这里是石宫寺的大雄宝殿。只见陡直的石壁上开凿出三个长方形的窟门,正中门洞上方,刻三个篆字“万佛岩”。进得洞中,迎面三尊大佛端坐于一米多高的莲台之上,每尊大佛身边都环立着弟子像,有的还有胁持菩萨像。八根一米见方的石柱,支撑起高达5.5米的穹顶,石柱上雕满大大小小的佛像,四壁也是密密麻麻造像森列,置身其间,仿若步入了佛国胜境。
钟山石窟群,现存大小洞窟18座,目前发掘了9座,但开放参观的只有6座。石窟的精华部分集中在第三窟,这里是石宫寺的大雄宝殿。只见陡直的石壁上开凿出三个长方形的窟门,正中门洞上方,刻三个篆字“万佛岩”。进得洞中,迎面三尊大佛端坐于一米多高的莲台之上,每尊大佛身边都环立着弟子像,有的还有胁持菩萨像。八根一米见方的石柱,支撑起高达5.5米的穹顶,石柱上雕满大大小小的佛像,四壁也是密密麻麻造像森列,置身其间,仿若步入了佛国胜境。
三尊主佛是石窟建造者最为精心的创作。每尊佛像均高3.54米,在这个进深只有9.5米的洞窟中,显得高大庄严,须仰视才见。据专家考证,这三尊大佛是依照三方佛的规范排列的,自左向右依次为东方净琉璃世界的药师佛、。这种规范化的解释已在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审批程序中得到认定,是标准化的说法。不过,有些研究者却依照对佛造像的直观感受,提出另外一说:,、现在世和未来世。这种说法虽不尽符合仪轨,但却因其更直观更形象而易于为当地人所接受,解说员自然也乐于采用这种讲法。我随着她的讲解仔细观察,似乎也看出一些门道——瞧,左面那尊前世佛,面容略显清瘦,头包缯巾,遮住了初现的头髻,双目微睁,袒胸赤足,大耳齐肩,法相庄严。左手抚膝,右臂上举,右手施说法印。脚下踩着两朵莲花正含苞待放。这些细节似乎在委婉表现佛祖成佛初期的情状。再看中间的现世佛,佛祖的头髻已然整齐排列,神态沉稳,似笑非笑。右手依旧施说法印,结跏趺坐于仰覆的莲台之上。此时,座下的莲花已经开放了。转来再看右边的未来佛,佛祖的头髻已呈螺旋状,半披袈裟,凝神静思,双手并拢施禅定印(一说为九品上生印),而座下的莲花已然全部绽开。单是一座莲台,古代的工匠们就如此殚精竭虑做出不同的安排,足见其谋篇布局之精审和细节刻画之精到。 ![]() 支撑这种佛祖三世说的证据,还有佛祖身边的那两位大弟子:迦叶和阿难。三尊大佛均以这两位大弟子为主要胁持,而他们并无三世之说。于是,时间的沧桑就被工匠们镂刻在他们的形象上——在前世佛的两旁,迦叶是个中年人的相貌,而阿难则是个少年小沙弥的形象。在现世佛的两旁,迦叶已经沧桑满面,几条皱纹清晰地刻在这位以苦修著称的佛弟子脸颊上,而阿难此时已是一个清俊成熟的青年人了。到了未来佛的身边,迦叶俨然是一个颓然老者,双目深陷,背已微驼,袒露的前胸一根根肋骨清晰可见,阿难则沉稳持重,一望而知是人到中年了。以弟子的形貌来表现岁月流变,用以衬托佛祖在不同时空中的形神风貌,可以说是钟山石窟的创作者独具匠心之处,也恰恰体现出石窟造像艺术从早期接受古印度雕塑理念的影响,经过隋唐时期逐步向中国化演进,到了北宋早期已变得更加写实、更加贴近民俗了。钟山石窟正处在这一变化过程的关键节点上,故而成为中国雕塑史和石窟建造史上独一无二且无法替代的艺术标本。
支撑这种佛祖三世说的证据,还有佛祖身边的那两位大弟子:迦叶和阿难。三尊大佛均以这两位大弟子为主要胁持,而他们并无三世之说。于是,时间的沧桑就被工匠们镂刻在他们的形象上——在前世佛的两旁,迦叶是个中年人的相貌,而阿难则是个少年小沙弥的形象。在现世佛的两旁,迦叶已经沧桑满面,几条皱纹清晰地刻在这位以苦修著称的佛弟子脸颊上,而阿难此时已是一个清俊成熟的青年人了。到了未来佛的身边,迦叶俨然是一个颓然老者,双目深陷,背已微驼,袒露的前胸一根根肋骨清晰可见,阿难则沉稳持重,一望而知是人到中年了。以弟子的形貌来表现岁月流变,用以衬托佛祖在不同时空中的形神风貌,可以说是钟山石窟的创作者独具匠心之处,也恰恰体现出石窟造像艺术从早期接受古印度雕塑理念的影响,经过隋唐时期逐步向中国化演进,到了北宋早期已变得更加写实、更加贴近民俗了。钟山石窟正处在这一变化过程的关键节点上,故而成为中国雕塑史和石窟建造史上独一无二且无法替代的艺术标本。![]() 所有石窟都体现着当时当地的思想和佛事现状,钟山石窟也不例外。钟山石窟因其开凿扩建的时间漫长,加之边塞地区五方杂处,往来的各族民众宗教信仰也有差异,因而石窟中吸纳和展现的思想也相对庞杂,华严、净土、禅宗、密宗等流派都有所体现。然而,依照台湾著名佛学家海云法师的说法,钟山石窟最精彩之处,就是用形象表现出宋代早期的思想。在他看来,钟山石窟满墙满柱都雕成大大小小的造像,这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宋代僧侣禅修的场面。修行所追求的是进入正定境界,一旦进入这一境界,其生命的本质就发生了转化。而钟山石窟正是对这一转化过程中修行者身、口、意三业的状态,进行了非常写实的描述与展现。
所有石窟都体现着当时当地的思想和佛事现状,钟山石窟也不例外。钟山石窟因其开凿扩建的时间漫长,加之边塞地区五方杂处,往来的各族民众宗教信仰也有差异,因而石窟中吸纳和展现的思想也相对庞杂,华严、净土、禅宗、密宗等流派都有所体现。然而,依照台湾著名佛学家海云法师的说法,钟山石窟最精彩之处,就是用形象表现出宋代早期的思想。在他看来,钟山石窟满墙满柱都雕成大大小小的造像,这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宋代僧侣禅修的场面。修行所追求的是进入正定境界,一旦进入这一境界,其生命的本质就发生了转化。而钟山石窟正是对这一转化过程中修行者身、口、意三业的状态,进行了非常写实的描述与展现。
海云法师说:“我所见过的石窟中,往往都在展现如何入定的坛城,唯独钟山石窟竟把入定以后的状况描述出来,可贵、伟大、了不起!就钟山石窟所表达的行法部分而言,它可谓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
依照法师的指点,我们把目光投向了那满壁的各式造像。现代人固然已无法进入当时的禅修境地,但是,从那些栩栩如生的菩萨、罗汉以及僧侣、供养人的形貌和动作中,我们不难体味到那种虔诚、庄重和心灵愉悦。那些造像,有的数尊成组,有的单独成龛,有的讲述故事,有的刻录说法实况,有的正与同伴切磋,有的只是静思冥想……了不起的宋代写实艺术精神,在这里得到了集中而精彩的呈现——望着石窟里那满墙鲜活的生命,我仿佛也被带进了千年前的那个静谧而神秘的佛国世界,陷入了浩渺无极的玄想之中。随着钟磬鱼鼓之声在时间长河中逐渐消弭,钟山石窟的宗教色彩如今已越来越淡了,反倒是它的艺术魅力愈发迷人,令人惊叹,令人倾倒。
先说其总体建筑设计。钟山石窟的主窟是在一块巨大岩石上整体设计开凿而成的。这就是说,古代工匠在开山之前,已经对这块巨石进行了精妙的设计,门洞、穹顶、柱石、莲台、主佛、胁持、壁龛等等,尽在他们的谋划安排之中。整个洞窟东西宽15.4米,南北深9.5米,高5.5米,总面积225平方米。八根石柱,三组主佛,都是预留的山体;开凿过程自上而下,层层开挖,顶端的空间开出之后,又为下面的精雕细刻提供了采光和通风的条件;巨型方柱既是整个大殿的支撑点,又是铺展造像的作业面,无形中拓展了造像的可用空间。在后排的四根石柱中,有些作业面刚刚打好草稿,尚未雕完,这倒恰好为后人提供了一个了解其造像施工过程的实物标本。
环视全窟,可见当年工匠们缜密的整体构思。在相对狭窄的空间里,竟然雕刻出7000多尊大小佛像,没有精巧的安排就会杂乱无章。而钟山石窟的设计可谓疏可走马,密不容针。三个门洞中间设计出两个对称的石雕墙,两段墙壁上的佛龛都是成对雕凿,十六尊罗汉分列两边,一边八尊,两两相对。窟内的三面墙壁全部用来造像,每一面都安排大小佛龛穿插:东西两壁较短,各安排高两米的大龛一组,且东西对称;窟后的北壁较长,则安排高两米的大龛两组,左右对照。佛坛前的四根石柱是进窟的视觉焦点,每柱各有两个佛龛,四周环绕无数小像,如众星拱月。有一面墙壁山体原有一个裂缝,石工们别出心裁,将大像化小,让坐佛起立,或者干脆雕成一尊睡佛,巧妙地将山体的缺陷化成灵动的画面。面对着如此丰富多彩的万佛会聚、主次分明且千年不朽的艺术宫殿,我们不能不惊叹这些古代设计师的构思运筹之妙。如此浩大的工程,能够如此有条不紊,循序渐进,调度有致,主次分明,足见古人不光具有宗教的虔诚和高超的技艺,更具有宏观设计和精密施工的运作能力。
石窟艺术的核心是造像和彩绘。钟山石窟的造像既不同于敦煌的木胎泥塑,又不同于云岗、龙门、麦积山的纯用石雕,而是以石雕为胎底,外用泥塑勾勒细部,最后施以彩绘。这种方法主要用于莲台之上的三组雕像,而墙面和石柱上的小型雕像,则都是石雕了。石胎泥塑加彩的制作方式是否为钟山所独有,我不敢轻易断言,但至少可以认定,钟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例证。石雕上面敷以泥塑,有利于刻画人物表情和服饰的细节,而细节表现恰恰是宋代写实艺术的审美要旨。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泥塑所特有的细节表现力,前面提到的迦叶和阿难的面容和表情又将焉附?如此说来,钟山石窟的石雕加泥塑的艺术手法,刚好也是与宋代写实理念相应相合的。
说到造像之美,钟山石窟确实看点多多。这里的菩萨绚丽多彩,婀娜多姿,显然是最夺眼球的。在莲台上有两尊胁持菩萨,身高略低于两位大弟子,但也高达两米多。左边的菩萨头戴花冠,面容俊俏,衣带飘垂,腰肢侧倚。可惜双臂已残,我们只能通过想象来弥补其曼妙的身姿了。右边的菩萨是全窟的美神,头上花冠高耸,中心有一小佛像,这应是观音菩萨的“标配”。微微颔首,似笑含羞,斜倚腰身,凸显曲线,胸前佩戴珠宝璎珞,腰间轻系红色飘带。右手已残,左手做说法印,跣足立于莲台上,其神态其身形其服饰其色彩,真是令人一见倾心。
有人说,中国的艺术一向偏重于阴柔之美,自隋唐以来,连原本男身的菩萨都被改造成妩媚的女神。单就我有限的目光所及,已有好几尊菩萨造像荣膺“东方维纳斯”的美誉,若山西大同华严寺的菩萨像,若敦煌莫高窟的菩萨像,等等。而雄强伟岸、充满力量的阳刚之美,却成了中国艺术中的稀缺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但是,在钟山石窟中,我们却看到了一些充满阳刚之美的雕塑作品。比如主窟须弥座下的那尊力士像,只见他肩负佛座,肌肉绷紧,青筋暴起,双目圆睁,浓眉竖立,脚趾扣住地面,身躯抵住重压,那种力量感和耐受力,看了令人振奋。而在钟山石窟的第五窟,还有一尊护法神韦陀的造像,海云法师对这尊韦陀评价极高,他说:“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石刻韦陀,是钟山石刻的造像艺术成就的代表。”![]() 钟山石窟就像一座刚被开采的宝山,其内涵和底蕴深厚而浩大,还有许多待解之谜,等待着人们去探索去发掘。我作为一个匆匆过客,虽然对钟山的诸多谜题兴趣浓郁,却无奈才疏学浅,时间仓促,实在无法一一破解,只能在此提出问题,略述管见,以期引起热心读者继续探索的兴致。
钟山石窟就像一座刚被开采的宝山,其内涵和底蕴深厚而浩大,还有许多待解之谜,等待着人们去探索去发掘。我作为一个匆匆过客,虽然对钟山的诸多谜题兴趣浓郁,却无奈才疏学浅,时间仓促,实在无法一一破解,只能在此提出问题,略述管见,以期引起热心读者继续探索的兴致。
来到钟山石窟,人们最感疑惑的是,究竟是谁开凿了眼前的这个石窟?比较简便的回答,自然是依照窟内的几则题记,如前文引述过的关于治平四年,“安定堡百姓张行者发心打万菩萨堂。”题记中提到了领头人张行者,而在明代《增建万佛岩塔记》中,“张行者”变成了“僧行者”,这个变化值得玩味。或许陕北方言中,张与僧有些谐音?或许这个张行者本身就是个僧人?依照常理,挑头开窟建寺的,多半是出家人。因此,我宁可相信后者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
在阅读相关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一个群体似乎需要格外留意,那就是驻扎在安定堡附近的边塞军人。还是先看窟内几则题记——
安定堡番落第七十指挥第一都长行李均自发虔心修菩萨二十尊,永为记。驻泊同州堡使第二十二指挥使李九自发愿心,修菩萨十六尊为供养。熙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题记。众多和士兵自发前来捐资造像,这在其他石窟中是罕见的现象。而这恰恰是钟山石窟特殊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安定堡一直是宋朝的边塞重镇,宋军与北方各游牧民族战事不断。就在治平三年,也就是石窟开凿的前一年,宋军和西夏军还在这一带发生激战,双方僵持日久,后续乏力,方各自退兵。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带的主要居民应该是驻屯的军人和为军需服务的边民。
那么,疑问也就随之而来:一边是杀伐血战,另一边却是捐资造佛,这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呢?其实不然。越是接近死亡,越是渴望和平;越是生命无常,越是冀望久远。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那些在战事倥偬中挤出自己的军饷和时间,前来修造佛像的官兵们,其实恰恰是钟山石窟最重要的一批建造者和供养人。
在钟山石窟岩壁上和当地文献中,记载了不少与石窟有关的诗词作品,其中有很多就出自守边将士之手,我们也不妨摘引一首以为旁证——
《游万佛岩有感》:“我今来防守,俄入一洞天。峰峻摩青汉,树低浮紫烟。步殿俗气脱,披甲壮心坚。连夜繁乡梦,何时振旅还。嘉靖岁次丙寅孟冬吉旦,西安后卫领班都指挥,韩禄记。”
边塞石窟自有其独有的边塞风情,万佛岩上汇聚了如此多的边塞诗歌,造像群里蕴藏着如此多的军旅之力,这在中国石窟建造史上无疑是一个特列。据此,完全有理由推断,钟山石窟是当时的一个军旅工程,至少有相当多的下级成为造窟的实际资助者,而更多的守边戍卒则充当了造窟的义务劳力,在钟山石窟的千年修造历程中,那些无名的戍卒边民的功绩不应被埋没,理应记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钟山石窟静静地横卧在陕北高原的大山深处,任凭千年风霜的浸染,依旧保持着其雍容华贵的风貌。它像一个隐在深闺的绝色佳人,文静内敛,不事声张,偏僻成就了她的神秘,岁月赋予了她的淡定,而这,不正是这座旷世奇葩的独特魅力之所在么?
![]()
本文刊发于2016年7月15日北京日报品藏版
![]()
古都热风老广场
本公众号发布或推送的所有内容,
除注明来源外,版权均属北京日报社所有。
![]()
北京日报副刊部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