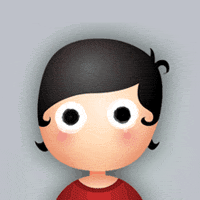【名人说名家】听马啸先生畅谈20世纪书画大师
在今天,将书法与绘画相提并论,已显得有些勉强。因为日益精细的社会分工,已将书与画推向了两条要求日趋不同的道路。因此,再以想当然的态度去推测如今一位画家的书法造诣,在许多情形下是不合适的。
但是,大约半个世纪以前,人们如果那样做,并无不妥。因为在那时,书与画的大分也尽管已露端倪,但极大部分画家都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培育和熏陶,并且人们仍必然地将书法的线条美作为绘画的基础,因此那时多数画家的书法功底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那些书画俱佳的艺术家,我们已无法也没有必要判定他们到底算是善书的画家还是善画的书家)。
世纪回眸,除去艺术影响属于上个世纪但依然在20世纪生活了20余年的画(书)坛巨擘吴昌硕,本世纪的中国画家中,给予中国书法影响最大的首推齐白石。这位木工出身的朴实艺术家,以他那一如其朴实个性般的大刀阔斧式的线条首先将中国的篆刻艺术推向了自吴昌硕以后的又一个新高峰。你或许可以断定齐白石用冲刀一挥而就的纵横驰骋的(石刻)线条,来自清代某位大师的某方印章。如赵之谦的“丁文蔚”一印。
形式的启发,但毕竟齐白石将原先的那种的偶然性发展、深化并完善成了一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使他成为本世纪的一位高耸入云的篆刻家。而这“篆刻家”三字又是由以下三个坚实的支点支撑的:长距离的冲刀方式;完善的整体构成形式;对比强烈的形式感和视觉效应。此三者,即便是此前的全能大师吴昌硕都不曾具备,比如在吴的作品中任意截取一字或数字,即可成一作品,且其与原先完整作品艺术效果基本一致,但若将齐的印拓割裂,那么作品也随之消亡——这便是齐白石篆刻的整体性所在。纵观数千年的中国造型艺术史,书、画俱能而又对印学有如此大贡献者仅二三人而已:赵之谦、吴昌硕之后,接下来便是齐白石。
齐白石的书法(指篆书)基本保持了篆刻的冲击力。大胆借鉴并采用汉代《祀三公山碑》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一发而不可止的高亢、雄壮气概。从更本质的角度讲,这是齐白石底子里的平民性格使然。正是这一点,使得这位大师成为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象征:深入浅出,变“阳春白雪”为“下里巴人”,与学究化、学院化告别。但齐白石作品的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粗率而少细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笔者更喜爱他的那些含米芾笔意、用笔丰满刚健又意态自如的行书题跋)。
比之齐白石的粗率,同一代另一位画坛大师黄宾虹的笔下周全得多。尽管从绘画看,黄宾虹的用笔比齐白石恣肆得多(而齐的许多东西却是工写合一),但这种“恣肆”是完全建立于那种千锤百炼、几乎无隙可击的传统基础上,因此他的艺术实践应正了那句如雷贯耳的传统格言:“从心所欲,不逾规矩。”这一点,你如果站在他的山水画前尚无法体会的话,那么面对他的书法,便一目了然了:如果说齐白石的率意可用一个“野”来描述的话,那么黄宾虹的率意则可用一个“逸”来概括。
黄宾虹 黄山杂咏
而此两种艺术个性,也正是整个中国传统艺术和艺术家的两大性格特性。
事实上,不论齐白石或是黄宾虹,都在一种新的时代氛围的感召下改良或推进传统,只不过前者“板着脸”工作,后者“和颜悦色”地工作。而这两种“工作”方法基本代表了自明末清初王铎、傅山以来中国书法继承、创新的两种典型途径,。
当然还有第三条道路,这便是张大千的书法创作方式——既融碑之刚劲又不失帖之圆润,既新创形式语言,又保留传统意韵。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也许可以说这位大半生奉行传统作画模式晚年又大胆借鉴西画形式感而热衷泼彩法的画坛大家的书法作品,其左低右高、上窄下宽的结体有时显得过于机械、过于程式化,但形式的创新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其用笔之严谨,章法疏密、错落之得当,节奏之和谐,几乎可看成本时代的一个范例。
事实上,我们也完全可以以绘画类比书法:张大千书法笔墨之精熟、章法之和畅恰与其创作传统形式绘画之得心应笔、一丝不苟与温雅和谐相一致;而个性特征鲜明的结体,正表证了一代大家心中萌动着创造冲动,正是这种冲动促使他后来大胆进行绘画形式的革新探索。
作为本时代书画俱能的艺术家的代表,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在书法领域内分别奉行三种不同的艺术创作模式,这是80年代以前整个中国书法的基本样式;同时我们也基本可以在他们的书法与绘画之间找到一种对应关系。但书与画的本质不同与发展的不平衡也由此显露苗头——张大千可以在“为古人作嫁”大半辈后突然“醒悟”,来个洋为中用,在与书法几乎同样古老的国画中引入西画的色彩效果,使得画风大变,而其书法的脚步则始终徘徊于碑帖之间(而当时东瀛书家已从事“现代”样式实践许多年)。书法的惯性的强大及其发展的艰难性由此可见一斑。
活跃在本世纪中国造型艺术舞台上画家中还有数位的书艺水平达到了一流水准,他们分别是徐悲鸿、吕凤子、潘天寿、陆维钊。
清末那个变法不成而躲进小楼的康有为,在其晚年为中国书坛培育了许多栋梁之材。徐悲鸿或许从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书法家,但其作品所显示的功力与艺术魅力,证明他不愧为康氏书艺的杰出继承并光大者。这里的“继承”是指徐氏在书法中继承了康氏稚拙而不加矫饰的碑学品格;“光大”是指他并非停留在康氏书风的形式外表上,而超越师长,自创一体。同时,与康氏作品对照,徐悲鸿的作品没有那种生涩感,更多的是婉转与温润。因此,徐悲鸿这独特的“一体”,既是兼容拙朴北碑书风与流丽的南帖书风之结果,又是揣摩的孩童书写习惯的结果。因此其书中并存着魏碑的劲健、帖学之婀娜与孩童般的天真烂漫。
用艺术学的观点看,徐氏的实践模式或许是中国传统书法发展的一种最具合理性也最有效的模式。
当然,徐悲鸿也不无给我们困惑:在书法中童心焕发、灵性四溢的他,在创作油画时那样小心翼翼、循规蹈矩。从教学的角度讲,这是一种必要,因为当时中国的现代美术教学体系刚刚着手建立,因此在其中贯彻一种严谨的学风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师却把“写实主义”原则作为中国美术发展唯一有效、唯一可遵循的原则,就无视了中国传统艺术中传承了数千年的写意精神——当他将那位对东方写意艺术极感兴趣的西方现代美术大师、“野兽派”祖师马蒂斯叫成“马踢死”时,大约没有想过自己的那些歪歪斜斜的汉字墨迹与马蒂斯油画笔下的单纯、稚拙的女人体都是遵循极为相似的艺术原则创作出来的。
事实上,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至六七十年代,追求稚拙的艺术风格,是许多有个性的艺术家的自觉行为,谢无量、徐生翁是书坛典型两例,在画坛善书者中最为著名者徐悲鸿外,尚有国画大家吕凤子。与徐氏不同的是,吕凤子书法之“拙”不是从孩童体中来,而是在行草书中掺杂了诸多的篆、隶古朴笔法的结果,因此若细细划定,其书风应算是“古雅”一类。与徐悲鸿一样,吕氏也是一位清代碑学传统的优秀继承和推进者——其既保留了先师李瑞清书风质朴、刚健的一面,又使用笔婉转而错落有致,全无李瑞清那般僵硬、刻板痕迹。
从徐悲鸿、吕凤子的书法实践中,我们看到自清中叶开始的那场“碑学”革命在其经历了两个世纪后的推进与深化。
与上述二人略有不同,潘天寿的书法则展现了其作为一个极富个性的艺术家的另一种能力:与众不同的造型能力。这位浙江美院(现中国美院)教授的国画作品有两个鲜明特征——清劲刚直的线条和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大反差布局,这也恰是其书法的特征。与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徐悲鸿及当时许多书家的作品相比,潘天寿的书法线条或许单薄了些,但这位国画大师在书法形式上所作的努力,是当时许多专事书法的人所无法比拟的。尽管以中国传统的艺术眼光评判,这种形式努力多少有“人为”的痕迹,因而很难达到自然无为、天机流荡的最高境界,但其通过结体、布局中强烈的疏密、俯仰、穿插、大小对比所表现出的节奏韵律,也正是那些书法大师梦寐以求、终生追求的。
这是他给予本世纪书坛的贡献。当然,站在书法本体的立场上看,潘氏的许多作品用意”太甚—他太着意于字形之结构,似乎想尽一切可能使之“出人意料”,以致没有时间来将笔意料之中或线条丰满起来,从而赢得一种更为内在也更为耐人寻味的力量。
本世纪已过世的书画俱能的艺术家队伍中,有一位终结性的书法集大成者,这便是浙美的陆维钊教授。虽然陆氏的绘画成就外界宣扬得不多,但其于山水及花鸟画创作中所显示艺术功底及达到的境界,表明这位书法大师于绘画并非仅是“爱好”而已。当然,与绘画创作中的温雅、冲和不同,陆氏书法充裕了一种激情和创造精神。尽管从外表上看,其书法的取法更多地来源于碑学,但他那完美得无隙可击的用笔、结体及章法,证明他在继承上的宽泛性。之所以说陆维钊是本世纪书坛的集大成者,主要基于以下三项事实:其一,真、行、草、隶、篆,诸体皆能,且无论功力或内在个性都极为突出,它们均可以“陆体”二字称之;其二,作品兼具多重性格,无论温和、典雅或是稚拙、豪放,均得心应手,成熟完善。其三,金石碑帖兼容,且形式新创与意韵和谐相得益彰,绝无生硬牵强或不伦不类之弊端。
活动在本世纪的艺术家中,在书法上有此成就且精于绘事者,几乎找不出第二人。
此外,还有像高剑父、丰子恺、陈半丁、陈衡恪、吴湖帆、李可染、李苦禅、王个簃、刘海粟等著名画家,于书艺也均有不同程度的建树,只不过他们各自或偏重于感情的挥洒(如高剑父、刘海粟),或侧重于传统模式的继承(陈衡恪、王个簃),或钟情于大众通俗易懂形式书写(吴湖帆),因而没有达到前文提及几位的高度,但也正是他们的存在构成了现代画家书法丰富多采的一章。
提起本世纪的学者书法,毫无疑问地,第一个想到的便是鲁迅(周树人)。的确,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战将的那一手刚健、饱满、含而不露、从容疏朗的墨迹,全可以看成那个时代中国知识精英人格、学养的一个象征——学贯中西、目光深邃、刚毅果敢而又从容不迫、诙谐风趣。如果不仔细品味这位从水乡绍兴走出来的文化战将的墨迹,你也许会发出“平淡无奇”的感叹,并怀疑其文(小说、杂文等)与字(当然是指书法)之间的一致性——平日里他笔端的那种愤世疾俗、嬉笑怒骂到那里去了?然而,当你真正深入其中,便会发现这依然是那个鲁迅,那个吃透了中国文化精髓、将人格的尊严与不犯贯注于笔端的鲁迅。
鲁迅的字与众多学者的书法不同,它更多的不是潇洒、随意,而是沉稳、含蓄。无论是信札、文稿或是给友人作就的条幅,总是一丝不苟、笔笔送到,并真正体现出中国书法“无垂不缩,无往不收”的艺术精神。
当然,仅此概括鲁迅书法的魅力是远远不够的,他的墨迹之所以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能吸引越来越多的观众——内地报纸争相集其字迹以作报名,此举便是明证——有赖于其用笔中金石味,即有如青铜器铭文般的镌刻美:许多转角和笔画的交叉处笔触厚实,似有漫患、粘合、风蚀效果。单从这一点看,这位文坛斗士于碑学、金石学已融会贯通、举重若轻了。
当然更全面的评价来自郭沫若先生:“鲁迅先生无心作书家,所遗书迹,自成风格,熔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系,世人宝之,非因人贵也。”(《跋鲁迅诗稿》)鲁迅书迹的金石气是其人格的写照。于20世纪,鲁迅的书法虽并不像的文章那样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心灵,但其笔墨之中所蕴含着的深沉、坚实的力量,可能只有李叔同、马一浮这样的文化大师级书法家才可以媲美。这是许多以“书法家”自居的人们应该感到羞愧或反省的地方。
民国时期,还有两位大学者的字以书风严谨而闻名,一位是章士钊,。与鲁迅不同的是,二人的书法追求的不是金石韵味,也不具鲜明、强烈的个人色彩。他们走的是一条传统的继承道路,因此并不急于从奇崛、斑剥的北朝碑版中寻找灵感或启迪,而依然在均衡、和谐、平正、循规蹈矩中获得心灵的满足和艺术的愉悦。正因为如此,二人于书法有着最大的相似之处:宗帖学、尚清雅。当然,差异也在所难免。章士钊更多地对唐代书法感兴趣,将欧阳询的挺劲与褚遂良的婉转合而为一,这样便在沉穆、凝炼中增强了几许活泼与节奏感。
,只不过比起赵字,马氏用笔更为纤细、修长,因而更显清秀与挺拔。
赵孟頫 洛神赋
同为知名学者,马一浮的艺术追求与上述二人有很大不同。如果说章士钊、、用笔优雅、和谐、雅俗共赏的一面,那么马一浮以他的最大能耐展现书法的另一面——生拙、突兀,令多数人不快。如果说前面二人作品的艺术性问题,以单纯的“艺术审美学”便可以研究得十之八九的话,那么马一浮的书法,不仅需要艺术学、美学,还需要更多、更深学问才能接近、理解。
从清末碑学大师沈曾植那儿借鉴、发展而来的马一浮书法,粗一看,是一幅不和谐的图景:笔触硬直、生涩,结体左低右高,骨骼外露……蠲叟(马一浮号)书法明显留有寐叟(沈曾植号)之痕迹,但就近细瞧,前者用笔更轻盈,更空灵,结体更俊丽,章法更疏朗。马一浮的魅力,是将北碑生硬的笔触、突兀的结构以一种虚笔或枯笔中饱含着的柔性的力量化解得无迹可寻,天机流荡。所以,你若没有真正的文化、艺术的修养,没的人生的阅历,是绝对无法辨识其中的美,当然更无法辨无识深藏其内的文化内涵。可以说,在20世纪的文人书法中,马一浮是最具文化深意、生命情致,同时最不易理解的一位。
中国书法自诞生的那一刻起,一直朝着一个既定的目标迈进,这就是更舒畅,更令人赏心悦目。这也是整个世界艺术的总趋势。但自从明末清初,尤其是清中叶碑学运动兴起以后,中国的书法艺术有了一种反向潮流:展示不和谐,或者说发掘“丑”的艺术价值。,古老的书法艺术重新获得了生命活力,同时它也以更丰富、更全面的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古老的书法艺术重新获得了生命活力,同时它也以更丰富、更全面的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也正是站在这一立场上,我们说,鲁迅、马一浮的书比之章士钊、,更令我们思索。
当代另外一名已故的大作家也值得书上一笔,他便是那位《子夜》的作者茅盾——沈雁冰。,由茅盾先生书写的刊名线条清畅、俊丽且法度井然,令人回味再三。笔者没有见过茅盾为欣赏目的而专书的书法作品,得见的多为文稿、信札,其间作者清新、简约的书风犹如春风拂面,一洗凡尘。在当代大文学家中,除鲁迅等少数几位外,很少有人能达此境界。茅盾书法线条修长、纤细,但长而不乱、纤而不弱,在那些细若游丝的笔画间,起承转合交待得非常清楚,且起、收笔及转折处抑扬顿挫,饱满而富节奏,绝无含混不清或拖泥带水之弊端。
而要做到这一点,对于一般人来讲起码面临三个难题:细,长,随意。茅盾的用笔似乎在挑战极限——纤细的行书极限。它使我们想起宋代的赵佶,他们都是以纤细的线条展示出一种别样的力量:优雅、含蓄、隽永。但赵佶仍不时地展示出一种尖锐(或尖刻),茅盾则完全是一种温柔的力量——它看去似乎纤弱无力,但却是绵里藏针。
作为两名无意作书家的作家,鲁迅和茅盾的成功,是一种真正艺术意义上的成功:无为而有大为。这是书法原意的回归。他们的那些手札墨迹,使我们不得不再次考虑这样两个严肃的问题:书法家应该怎样做?书法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注:德玺堂艺术生活馆经马啸先生同意发布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