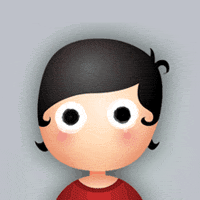无法面对的事
在甘肃山区,最近,有一个贫穷的女人杀了自己的四个孩子然后了,其中包括一对双胞胎,别的都是毒杀的,最大一个孩子看出母亲的杀意想逃走,被斧头砍中,伤重不救。他们的父亲回家,料理完所有人的后事,也了。这个母亲姓杨,生前据说是一个温和爱笑的女人。
在香港,有一个以会名义发起的戒毒组织,他们以为戒毒的信念和力量。我听过关于他们的一个故事,在知乎关于毒品的危害的提问中看到的,不知真假:其中一个牧师,笃信上帝,戒毒戒了二十年,几乎半辈子,并拿自己戒毒的事例劝诫过不少人,最后临了了,临终做忏悔,他最后一个请求竟是,“你能给我再注射一针吗?”
无法面对的事。
看完这两个事例,我久久无言。这两个故事,是先后看的,后者,具体看的时间我都忘了,前者是这一周才看到,但它们都让我无言。
面对这两个故事,我找不出能够劝说的渠道,能够理解的方式,能够解决的方法。
对别的事情我有。我看《密阳》,就是之前公众号里说过的,那部韩国电影,我纠结了一年,但最后其中的疑问我能解决。
中的宇宙观,《时间简史》里对于这个世界的疑问,信或不信,唯物唯心——这些问题我是不能尽然解决,但我也没想解决。我的心告诉我,世界有神明,那我就信仰神明。我不想在终极问题前,扮演哲人。
至于加缪的“西西弗斯陷阱”、尼采的狂人狂言,我也只当做精神不健全的病人言,他们自己都过不好自己的人生,又何必以他们的毒素荼毒我的理念。原谅我这么说显得很自私,但事实就是,世界上,有的人你愿意去理解,有的人你不愿意去理解。
然而这两个故事中的两个问题,我都解答不了。
第一个故事,我最初看见它,是在我的朋友龙薇转载的一个哲学公众号里。实话说写那篇文章的人我很不喜欢,她说杨不是变态,她是清醒而绝望的人。但我要说,“清醒”和“绝望”这两个词,太轻;在你笔下那个文字世界,所能涵括的一切,都太轻。
如果你真的经历过痛苦,那种切肤切齿的让你连一分钟都捱不下去恨不得立刻的痛苦,请你告诉我,什么叫绝望,什么叫清醒?
感觉到自己逃不出地狱就叫绝望吗?知道自己逃不出地狱就叫清醒吗?——如果,“感觉”和“知道”就能使一个人堪称为人,那为什么一个人,要做出人所不能为之事?为什么一个人,要毁灭掉人之所以为人所依恋着生存的东西?
——杨在杀人后特地去看访她的父母,父母悲痛欲绝,她只是说,“孩子活着对你们也是负担,再说他们大了,迟早也要走的,是要抛弃你们的。”
这句话的潜台词,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既然他们迟早要抛弃你们,何不如现在就死了呢?
这是曹禺《日出》里所写的那个无望中毒死儿女的黄省三吗?
这是现实!这不是!
后者我则更不必去说。一个笃信着宗教的人,一个能用极强的意志力控制自己不接触毒品、长达二十年的人,临终时他生存的负担一放,他第一个想的,竟还是去触碰毒品。太忍不了了,不能忍啊,毒品带给人的是什么?——那是直接刺激人神经中枢的欢愉,那是直接在人大脑皮层的电影屏上跳舞的极乐,或者不如说,那就是魔鬼用它的魔掌拟造而出的,宗教中的极度天堂。只不过,天堂给人的快乐是安宁和平静,毒品给人的快乐是膨胀和狂热;天堂许诺以人永恒,毒品只给人瞬间。
我恨那个牧师,却不能唾弃那个牧师。我恨他,是因为他亲手毁了他自己的信仰,也毁了别人的信仰:他就在一刹那还是让魔鬼夺去了他的灵魂。他的举动等于亲口向全世界的人宣告,听着,你们再也不必有信仰了,你们所信的东西不过是马克思所说的精神鸦片,是为了保障你们此生中那廉价的安全感;而一旦死亡到来,人类再也不必背负上生存的责任,人还指望什么呢?所以,你们这些人,你们不过就是见风使舵、有奶就是娘的贱人!你们从来不信奉任何事,你们只依附着那些能让你们得到利益和快乐的东西!
然而我无法唾弃他。
我并未经历过他的经历,我也绝对不想,我又如何能唾弃。
所以,所以,我不能当着自己的良心谎称我爱杨,我原谅杨,杨杀的既不是我,我又如何有原谅她的资格?我既不是上帝,我又如何有原谅杨的权力?她清醒而绝望吗?我们就不清醒而绝望吗?清醒又意味着什么?绝望又意味着什么?到底多重的“清醒”才可被称之为“绝望的清醒”,又到底多重的“绝望”才可被称之为“清醒的绝望”?又到底,多沉重的苦难才能让人有被描绘为“清醒而绝望”的条件,从而获得作恶的特权?又到底,我们比起别人是占据了怎样的幸福,甚至是可耻的幸福,以至于我们无权利于罪恶面前谴责他们?!
所以,我也不能当着自己的良心,谎称我愿意去以自己的灵魂担保那个牧师,我做不到冒着自己也下地狱的责任,去对着上帝说,在终极审判的时候,对那披挂着大白翅膀的天使说,原谅他啊,米迦勒!因为他仅仅是软弱;然后侧过脸对着上帝:他既然信仰了你,圣父,那他就是无罪的。
我做不到。
因为我知那亲手杀子的行为是极恶,因为我知那临终求毒的言辞是背叛。
我知人自己无法原谅的事情里,就包括有极恶和背叛。我们无权轻言宽容,既然我们做不到原谅别人杀害我们的亲人,原谅爱人背叛我们的约定。
那何谈苛责于神?或说,灵魂?
可我亦做不到轻言质责,因为我没有经历过和他们一样的,神魂的挣扎。我不会对杨加以“清醒而绝望”这些莫名其妙的词,我能感觉到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她在做那件事的时候——杀掉自己的全部孩子的时候,她的脑海一定陷入了狂风暴雨、版块迁移一般的地质灾难里,一切都变了,原本没通电的区域通上了极热极其强烈的脑电波,一切都变了。
顾城说,他曾梦见过一句诗,“你是一个暴行/
我也不会对那个在临终时乞求毒品的牧师说上什么话。我无法怜悯他,也无法判他为背道之人,那我只有转过脸去,祈求我这一生都不要有类似的遭遇。
这就是我的灵魂里,唯一的真话。
最后我想说,这些东西,可以被付诸为文学作品吗?我想是不可以。文学途中,确实有许许多多的人,哲人先贤、文坛大师们,他们试图写过“无法面对的事情”,并试图将这些事转化为“可以面对的事情”,譬如《复活》和《罪与罚》。其中写的最对头的,我读过其作品的名人里,唯两人,一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人是太宰治。前者写,骄傲狂慢到极致的拉斯科尼科夫,终究在谦卑悲怜到极致的索尼娅面前跪下;后者写,“神一样纯洁”却始终无法融入世间和世人相爱的“好孩子”叶藏,在几度阮籍穷途之后,娶了一个在他眼前秉有对人“纯洁的信任”的妻子,却目睹妻子被人毫无感情地玩弄,从此变得战战兢兢,彻底失却了对人的信任之心,而在那个目击罪恶的晚上,叶藏的额头上像从此烙上了撕不去的神之封印,他丧失斗志,一夜白头。
我喜欢太宰治,因为他接受和承认了自己,永远都有那许许多多的他自己面对不了的也做不到的事情,他不说谎,虽然他也不做好人。
我崇敬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他逼迫自己将无法面对的罪恶转化为他灵魂里可以接受可以理解的事,所以他说,“在基督和真理之间,我永远选择基督”——但转而他又驳问自己:“难道在你心里基督竟然不意味着真理吗?”所以他笔下的伊凡疯了,公爵退回白痴,圣徒一般的佐西马长老没死三日就尸身恶臭——他的生命不足以让他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三部曲写完,这也许是遗憾,也许他本可以尽他的力解答出更多的“无法面对之事”,但他的肉体此生终还是不允这件挑战巴别塔的事由他一人独力完成。
但我爱托尔斯泰。因为只有托尔斯泰,他写了那个自私得让我心悸又软弱得让我心痛的安娜·卡列尼娜,她被痛苦所摧毁,被嫉妒所折磨的时候完全丢失了温文尔雅的本来面目,她变得如此颠沛,如此狰狞;不仅如此,他也写了那个看似身为被背叛的丈夫完全有权利标榜自己,却形同一个委曲求全的伪君子的安娜的丈夫,卡列宁,他为了道德的完全,宁可对安娜放手,却被安娜蔑视,心想:“你还不如干脆提出决斗!”——但卡列宁有错吗?他才是受害者。安娜的背叛没有撕毁他的灵魂吗?难道安娜的灵魂才是灵魂卡列宁的灵魂就不是灵魂?
我爱托尔斯泰。因为他写不完美的人,他写了那些不完美到有罪有罪到无法原谅的人,当然了,他也写了《复活》,写了他理想中的救赎,和原谅。但这个固执倔强的老头儿终还是选择了那条通往冰冷荒原的路。他的此生中,既有一面是愿和农民同劳作、放弃吃肉并坚持食素;亦有一面是曾如其他同时代的贵族一般放纵情欲,糟蹋过女人的肉身,以其冷漠狠狠地伤害了他的妻子。但我最终看到的却是这个无法救赎自己的人的热泪盈眶,他那双老眼里装满了因无法原谅自己而兴起的泪水。他走到了人的尽头,他发觉那不是神的尽头。
文至最后,想起最近在“读首诗再睡觉”中看到的荐诗言,我就不引用了,大意是,美杜莎的眼睛会让看到它的人被永恒凝固,而勇士通过镜子判断出美杜莎的方向,并在不必看清楚她的容貌的情况下刺杀了她,而文学就是那面勇士手里的镜子,美杜莎之眼就是可怕的生活。比喻很巧,但我不喜欢这个比喻。我永远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无法面对的事,我也永远相信我们可以在无法面对的事之外生存着:未必非得去充当屠龙英雄或审判官,非得跳入那永恒的深渊里,并高傲地爬出来,我们才有资格活下去——就像那不止一个为了证明自己能胜过毒品,亲自以身试毒并不可自拔地沦陷下去的缉毒警官一样。在这时我愿意承认自己的局限,和自己的软弱。我们是人,而且永远是人。